|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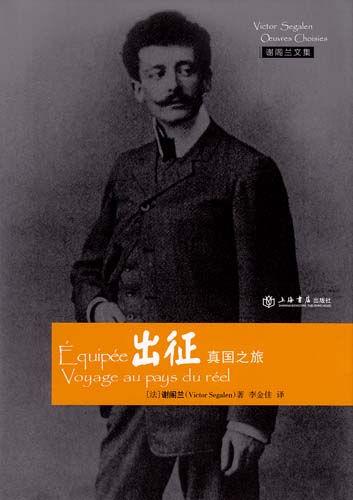 当维克多·谢阁兰构思《出征》时,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或已完成,或已着手创作。一个读者,若是读过《太古者》、《两个兰波》、《异域情调论》、《享乐主》,连同《想象》集中那些小说,以及《大河》、《碑》、《画》与《颂》,《天子》与《勒内·莱斯》,或者谢阁兰的旅行日记,或者他的论文《伟大的雕塑》,或者像《西藏》这样一部虽在1917年的旅行中诞生、可却萌芽于此前历次旅行的作品,那么,这位读者就不会把《出征》当作谢阁兰作家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而是将其视作这个生涯的一大总汇,概括着、反映着它的全历程。这不仅是因为在《出征》的本文同谢阁兰其他作品之间,存在着许多主题上的回响;而且因为谢阁兰在这本书里,回到他的作家兼旅行者这一双重活动上头,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究词语的能力、想象的威权、认识的限度、存在的基础,探究十年间不断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滋养他文学创作的所有问题。而这样探究的同时,他也就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景,反映出贯穿这风景的重重疑问,以及正在那里酝酿着的各种变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构成《出征》一大脉络的互文参照系统上。以“真国之旅”的形式,《出征》呈现给我们的,也是一次穿越文学的旅行,而其间又加上了一场对诗艺的阐发。 当维克多·谢阁兰构思《出征》时,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或已完成,或已着手创作。一个读者,若是读过《太古者》、《两个兰波》、《异域情调论》、《享乐主》,连同《想象》集中那些小说,以及《大河》、《碑》、《画》与《颂》,《天子》与《勒内·莱斯》,或者谢阁兰的旅行日记,或者他的论文《伟大的雕塑》,或者像《西藏》这样一部虽在1917年的旅行中诞生、可却萌芽于此前历次旅行的作品,那么,这位读者就不会把《出征》当作谢阁兰作家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而是将其视作这个生涯的一大总汇,概括着、反映着它的全历程。这不仅是因为在《出征》的本文同谢阁兰其他作品之间,存在着许多主题上的回响;而且因为谢阁兰在这本书里,回到他的作家兼旅行者这一双重活动上头,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究词语的能力、想象的威权、认识的限度、存在的基础,探究十年间不断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滋养他文学创作的所有问题。而这样探究的同时,他也就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景,反映出贯穿这风景的重重疑问,以及正在那里酝酿着的各种变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构成《出征》一大脉络的互文参照系统上。以“真国之旅”的形式,《出征》呈现给我们的,也是一次穿越文学的旅行,而其间又加上了一场对诗艺的阐发。
《路条》中有一部分叫“真国之旅”,是从1914年5月3日开始写的。在这个部分里,谢阁兰抛下考古学家的种种烦忧,专心制订起他的文学写作计划来。“真国之旅”的开头一段,为《出征》草定出这样的提纲:
Ⅰ.出发之前。我在想象中统治。
Ⅱ.出发。三个月间猛地浸入使人窒息的真实。——窒息着想象。
Ⅲ.而后,渐渐地,虚设回归[……]。
过了几行,谢阁兰又粗略地勾画出另一个提纲:同前一个提纲一样,它也计划先写真实在旅行一开始时就控制了“我”(“一旦向着真实进发,我就猛地被它攫住,除了它什么都再也感觉不到。”),而后写想象的反败为胜(“渐渐地,非常微妙地,一阵拍击声发自想象的后院”)。旅行的这两个时段,确实在《出征》中复现出来,并引领着读者:我们读到作者起先如何假装归顺与想象针锋相对的现实,然后又如何将摹仿性的文学斥为骗局,如何展示了想象富于创造力的权能。从这一点来看,《出征》似乎很可以视作谢阁兰一贯的美学信念的申明,而这一美学信念也是后马拉美一代的许多作家共同奉有的。不过,应该赋予这两个时段以什么样的继续和了结,这却颇令谢阁兰踌躇了一番:第一个提纲这样预计道:“真实同想象和谐地错织在一起,或者猛烈地对抗着……”;第二个提纲的说法更斩决些:“在一段时间后:拉锯战。而后想象获胜,击败对真实的‘回忆’和‘乡愁’”(卷Ⅰ,第1159页)。这种犹豫不决——在《出征》的本文里它被扫出视野,因为作者最后拒绝在争执的两极问做抉择——使我们不禁发问:谢阁兰在拟下这些提纲时,是否还感到囚囿于一种修辞学,虽然旅行的具体经验正在摇撼这修辞学,正在使他看到一线和解写作与世界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