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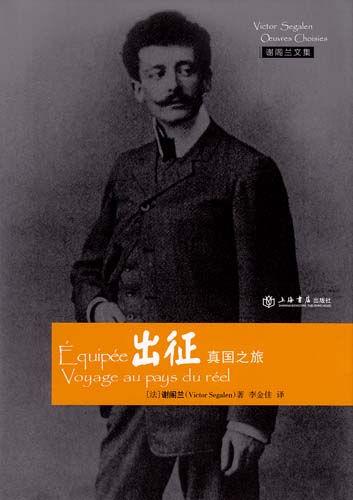 对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重读和再评价,是近五十年法国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一件大事。今天,我们谈论近现代东西方文化、文学交流、乃至这一交流所引发的诗歌流变时,迟早总要说到谢阁兰。许多评论家认为,谢阁兰以他全部的写作和生活赋予“异国情调”这个概念的充满个性的新意义,无论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来说,都是至今为止东西方交会所产生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从1990年代起,谢阁兰的小说和诗集开始翻译到中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的确,奠定谢阁兰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几部作品,都同他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经历密切相关。 对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重读和再评价,是近五十年法国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一件大事。今天,我们谈论近现代东西方文化、文学交流、乃至这一交流所引发的诗歌流变时,迟早总要说到谢阁兰。许多评论家认为,谢阁兰以他全部的写作和生活赋予“异国情调”这个概念的充满个性的新意义,无论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来说,都是至今为止东西方交会所产生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从1990年代起,谢阁兰的小说和诗集开始翻译到中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的确,奠定谢阁兰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几部作品,都同他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经历密切相关。
谢阁兰早年接受正统的医学教育,一生以行医为业,可是他的志趣,却全在文学、艺术和哲学方面,这在1898年至1902年他就学于波尔多海军医科学校的时候,就已露出端倪,并且随着他人生的进展,愈来愈显明。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谢阁兰就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诗人和思想者,他一生的交游与写作,也主要是面向巴黎的文化界,努力求得其他文学家、艺术家的承认。谢阁兰这种人生定位第一次与中国钩连,是在1902年他大学毕业后,作为海军一等医师,随都兰号赴任塔希提岛的途中:当年十月,途经旧金山港时,谢阁兰因身染伤寒,不得不在当地羁留一个多月;病后修养的空闲,他每每在当地的唐人街度过,华侨的生活、风俗、手工艺,特别是戏剧,都引起他兴味盎然的观察。这样,当谢阁兰结束海外任期,在1905年回到法国,开始比较密集的文学创作,渐渐熟悉了巴黎文坛的路数,并且不可遏止地厌恶起充溢着文坛的浮华而沤滞的风气时,他就渐渐萌生了去远东——对他来说那里代表着巴黎的反面——任职的念头。从1908年5月起,谢阁兰开始学习汉语,受业于东方语言学院微席叶(Arnold Vissiere)教授,在法兰西学院旁听著名汉学家沙畹(EdoLlard Chavannes)的课,并结交了考狄(Henri Cordier)、拉卢瓦(Louis Laloy)等汉学界人士。1909年3月,谢阁兰通过了海军部“见习译员”的考试,以进修汉语的名义调任中国,于同年4月从马塞出发,6月中旬终于抵达很久以来就魅惑着他的北京。此后的5年问,除了几次回法休假和在日本、东南亚的短期旅行,谢阁兰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一直到1914年8月他因一战爆发的缘故被召回欧洲。在华期间,谢阁兰先后作为法国驻华使团的见习译员、北洋医学堂的教官,袁世凯长子的私人医生,居住在北京、天津、山海关、河南彰德府等地,并且多次在中国各地旅行,可以说对当时的中国,他有着比较广泛和近切的了解。在中国的这五年,是谢阁兰文学创作的旺盛期,他的诗集或散文诗集《碑》、《画》、《颂》、《西藏》,小说《天子》、《勒内·莱斯》,还有这里翻译的《出征》(Equipee),都完成或酝酿于这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