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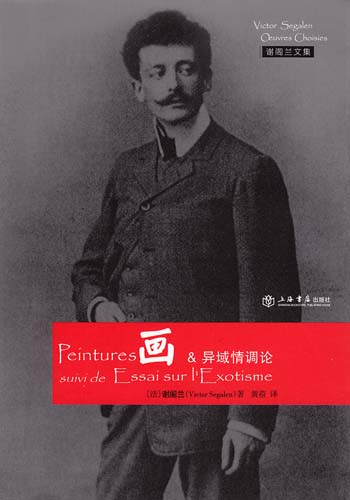 将中国画请进文学的殿堂,在20世纪初的欧洲,此举绝非寻常。日本的浮世绘在印象派画家的推崇之下在欧洲已经风靡了半个多世纪,而中国绘画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1909年,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举办了法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的中国画展。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当时已以海军医生兼译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但有幸得到了吉美画展的目录。两年后开始撰写并于1916年出版的散文诗集《画》将留下这个画展的记忆:一幅归于南宋画家马麟名下的《群仙会诲图》演变为书中的第一幅“玄幻图”;而一幅归于宋徽宗名下的《明皇教子图》则被列在十七幅“帝王图”中,只是画中的唐明皇变成了宋理宗。 将中国画请进文学的殿堂,在20世纪初的欧洲,此举绝非寻常。日本的浮世绘在印象派画家的推崇之下在欧洲已经风靡了半个多世纪,而中国绘画在当时的西方世界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1909年,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举办了法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的中国画展。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当时已以海军医生兼译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但有幸得到了吉美画展的目录。两年后开始撰写并于1916年出版的散文诗集《画》将留下这个画展的记忆:一幅归于南宋画家马麟名下的《群仙会诲图》演变为书中的第一幅“玄幻图”;而一幅归于宋徽宗名下的《明皇教子图》则被列在十七幅“帝王图”中,只是画中的唐明皇变成了宋理宗。
然而,读者大可不必为这部作品中的每一幅中国画寻找原型。《画》的开场白中,作者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是言说的画”,并有意强调:“诸位,你们果真没有失望吗?果真不是在等我描述确有其实之画?在我即将道出的字句后面,时而有真实的物象,时而有象征的画面,还常常有历史的幽魂……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开心?即使文字后面找不到色彩与线条构成的画面……那好,就让文字本身来作画,而且画得更加酣畅淋漓!”确实,谢阁兰笔下的画能在现实中找得出实物的寥寥无几。除了上文所举的两例外,《大明皇子宴戏图》的原型是作者自己收藏的一座屏风,《元朝的游戏》的开首部分可以从巴黎塞努奇博物馆(Musee Cernuschi)收藏的一幅归于赵孟頫名下的蒙古骑手图里找到点影子——谢阁兰将此画的印刷图片粘附在《画》的手稿里;《北周的上帝》则与日本京都仁和寺所藏的一幅佛教画极为相似。此外的绝大部分“画”在现实中都找不到影子。它们之所以为“画”,并非因为文字对实有的绘画进行了临摹,而是因为文字取代了丹青,以文学特有的手段勾勒出一幅幅画面。于是,作家成了画家;而对文字画面的观看,对读者来说,则“是融进画家的运笔,是在画面空间的漫步,是体验画中人的一招一式”;换言之,是进入画的世界、作品的世界、想象的世界。而作品中,画家又摇身一变,成为街头戏子,欲向围观众人展示手中的宝贝。这便是《画》的开头:“……你们在这儿,你们在等,可能已经下了决心。听我说到最后;可是诸位,你们可会好好地看,大胆地看,一直看到最后?……你们将要看到的是些中国画;长长的,发暗的帛画,带着来自远古的松烟与色彩。”
这些用文字勾勒出的中国画被分为三类:“玄幻图”、“朝贡图”、“帝王图”。“玄幻图”中的“玄幻”二字固然是指宗教、魔法等题材所产生的灵异氛围,但更是对所有与现实相异的世界的概括,尤其是艺术创造的世界。朝贡图、帝王图都是常见的宫廷绘画种类。《画》的取材主要有三大来源。它首先来自于作者对中国绘画本身的细致观察。谢阁兰的“中国画”就形式而言,不仅有挂轴手卷,而且有壁画;就材料而言,不仅有丝帛纸本,而且有扇面、瓷器、漆器;就题材而言,不仅有四季,还有道释、帝王、鬼仙等多种类型。《画》的第二个取材来源是作者在中国的游历与考古经历。自1909年来华之后到1916年作品出版之前,谢阁兰在中国做过两次长途旅行:1909年8月到1910年1月间,他从北京出发西行,经过五台山、西安、兰州,而后南下到了成都、峨嵋山、重庆,最后从长江顺流而下直到上海,跨越了半个中国;1914年2月到6月问,他又先入陕西,后进四川,进行中国墓葬艺术与佛教艺术考察。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的风俗、地貌、历史都有了异常深刻的体验。在其本人为《画》撰写的作品介绍中,谢阁兰特意声明“作家的身后有一个旅者,甚至可以说是探险家……《画》(‘朝贡图’)中的十行文字所包含的字数还不及走山路的天数多。而‘帝王图’中,《东汉的狂奔》则是在四川两个月考察之所得。”《画》的第三个取材来源,也是最重要的来源,是对法译中国典籍的阅读。谢阁兰几乎遍览了所有当时的法国汉学文献。“玄幻图”结尾的四季图无疑是对顾赛芬神父所译的《礼记》中《月令》一章的改写;“帝王图”开篇部分有关孔子观画的故事来自于考古学家沙畹的著作《中国北部考古》中《孔子家语·观周》的译文;“帝王图”中的大部分篇章与“朝贡图”中的一部分得益于戴遂良神父编译的《历史文选》。除此之外,戴遂良神父编译并作序的《哲学文选》、《道教》、《现代中国风俗志》(唐以来历代志怪故事选译)等汉学文献也都给予了《画》以直接或间接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