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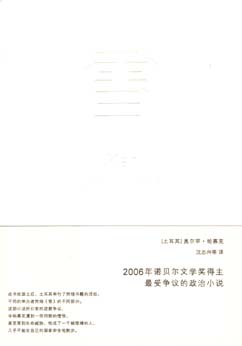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于5月21日-31日访华。除北京之外,帕慕克还走访了上海、杭州、绍兴等地,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在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同时,帕慕克的率性而为也让陪同者瞠目。本版的两位作者既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也是此次接待客人的主人,陪同帕慕克走完了访问全程。近距离接触帕慕克之后,应邀为本报再行解读帕慕克其人其作。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于5月21日-31日访华。除北京之外,帕慕克还走访了上海、杭州、绍兴等地,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在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同时,帕慕克的率性而为也让陪同者瞠目。本版的两位作者既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也是此次接待客人的主人,陪同帕慕克走完了访问全程。近距离接触帕慕克之后,应邀为本报再行解读帕慕克其人其作。
当然,所谓解读,有时也不过是勉为其难的一种认知,而任何人和事,远比我们所能了解的丰富和复杂。
首先要交待的是文章篇名受到了法国电影《父亲的荣耀》的启发。
在帕慕克心中,世界公民代表了最高的境界。不过,来自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家不大会在意自己是否表现出世界主义的胸襟,是否超越了地方文化的局限,或许对世界公民身份的渴望本身特别容易产自非欧美国家。我认为帕慕克的好恶和思维模式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征,在读其书知其人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当然,称他为一位土耳其作家,是对他以及他的祖国表示深深的敬意。
画册与普世价值
帕慕克写书,也喜好藏书。据他自己在社科院举行的作品研讨会(5月23日)上说,他的图书多达一万五六千册,其中不少是艺术门类的书籍。
5月30日下午,他在上海书城参加签书义卖活动后,又到书店的艺术类部门逗留了不少时间。同事告诉我,帕慕克几天前在参观故宫博物院时对中国传统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30日上午又去了上海博物馆,很是兴奋。“我还想看看有没有适合放在茶几上的画册。”他在上海书城对我说。
“八大山人”,“四王”,这些称谓他好像都知道。林风眠的生平他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对林的油画创作他的评语脱口而出:“中西结合。”大概类似的表述他已经听得太多,这次来个先发制人。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彻底抛弃了“继承、发扬传统”之类的话语,不东不西或东西调和是世俗领袖的梦魇,非此即彼的选择才合乎正道,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在各方面取法欧洲。于是我们用于称赞的“中西结合”从帕慕克嘴里出来(像背书一样)却可能是暗含贬意的。我向他推荐清朝意大利裔宫廷画家郎世宁作品集,他已经浏览过了,提不起兴致。也许这位米兰耶稣会教士的折中妥协的画法是最没出息的艺术“磕头”?帕慕克眼里的好奇蒙上了一层疲惫,我想用吴昌硕和潘天寿来给他一点刺激,只见他草草翻过画册,嘴里嘟哝着:“都差不多。”要是告诉他这两位中国画家的代表作在拍卖会上的价钱,那将是不大礼貌的行为。
我突然意识到,没有较高程度的“前知识”,欣赏国画大师的线条与色彩的神韵大概是很难的。换句话说,国画名作的价值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建构出来的,不具普遍性,并非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指而可识,一目了然。这道理应该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即使是威尼斯画派注重逼真性的作品,也不是任何人都会像“姨父”(《我的名字叫红》中的人物)那样佩服得不留余地。我认识的一位安徽小时工并不以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就是美的化身,这和帕慕克看待吴昌硕、潘天寿的方式可有一比。以往,那位小时工来打扫卫生时我会播放一些歌剧选段,以减轻各种杂音的干扰,现在我不敢了。有一次她感到忍无可忍,终于开口:“这东西听了像鬼叫,怎么关掉?”我在吃惊之余倒也受到了一些启发:原来西洋歌剧的动听也只是相对而言。既然如此,威尼斯画派也必定承受不了帕慕克欲赋予它的不言自明的普世价值。
但是帕慕克依然惦记着书店和画册。5月31日下午4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座谈会已经结束,飞机要到晚上8点半起飞,正好利用这点时间继续逛逛扩大了无数倍的“十里洋场”。帕慕克想再到福州路的书店看看,然后去浦东观赏摩天大楼,隔江眺望浦西景色。黄浦区和陆家嘴,鱼和熊掌最好兼得。我和两位朋友直接到浦东滨江大道选定观光点,结果在“上海码头”沿江的桌旁坐了下来,帕慕克则由上外老师陪同先去购书。
帕慕克出现在“上海码头”时脸上挂着一丝阴郁,西下的太阳给他留下了长长的影子。使他遗憾的是书店之行太匆忙。原来以为他会在高楼林立的地方拍很多照片,毕竟现在的陆家嘴已经不会输给曼哈顿了。不料他那只已经很有名气的数码相机居然没有现身。高大的帕慕克拎着他的公文包踽踽而行,若有所失。他在意大利绘画和细密画背后读出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中国画又是何种主义或意识形态的产物?现世主义还是唯美主义?希望他没有拿这类问题折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