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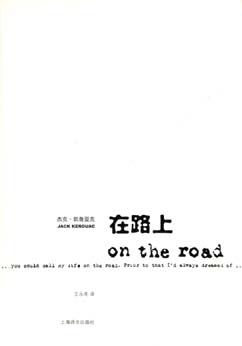 海明威的古巴故居、福克纳在孟菲斯的出生地——都是文学青年们朝觐的文学圣地,而凯鲁亚克在马萨诸塞的出生地洛维尔,却吸引了各色人士前来顶礼膜拜,有文学青年、摇滚乐手、画家、演员、观光客等等。凯鲁亚克也成了这个衰败的工业小镇最大的一门生意。凯鲁亚克远不只是属于文学。 海明威的古巴故居、福克纳在孟菲斯的出生地——都是文学青年们朝觐的文学圣地,而凯鲁亚克在马萨诸塞的出生地洛维尔,却吸引了各色人士前来顶礼膜拜,有文学青年、摇滚乐手、画家、演员、观光客等等。凯鲁亚克也成了这个衰败的工业小镇最大的一门生意。凯鲁亚克远不只是属于文学。
大门乐队的键盘手瑞·曼萨克说过,没有《在路上》,这个伟大的乐队就不可能存在;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中也写道,“《在路上》是我年轻时代的《圣经》。”《在路上》在50年前的横空出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摇滚的世界、性和药物的世界,以及紧跟凯鲁亚克车轮而涌上高速公路的车轮世界。
摇滚的一代捎带着凯鲁亚克的书上路了,但小说并非是一部摇滚圣经,凯鲁亚克本人也与摇滚不沾边。事实上,作为上世纪50年代反叛者的凯鲁亚克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上世纪60年代生活方式的先驱体验者——东方宗教式的冥思、大麻、四处为家,以及一点点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毁灭。这确实很酷。
现年88岁的劳伦斯·费林盖蒂是“垮掉的一代”老巢——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的创始人,他曾这样说过,“当你18岁的时候读到《在路上》,这棒极了;当你35岁或者50岁的时候读到《在路上》,小说中滥溢的浪漫和旺盛的精力,让你感到很不自在。”小说《在路上》今天正好50岁了,还好它的主要读者都在18岁左右,他们或者正准备上路,或者已经上路,更多的只是梦想上路,所以他们需要《在路上》绚烂他们的上路之梦。
出版于1957年9月5日的《在路上》描写的其实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一群特定年轻人的流浪之旅,这些出身中产的年轻人原本可以顺利地从常青藤院校毕业,然后加入父辈们的行列。但最终他们选择背叛,怀揣着可怜的几个美元,从东海岸奔向自由的旧金山,从新英格兰颠簸到墨西哥,没有目的地。“垮掉的一代”在路中,安于清贫,藐视权威,“不听命于政府,也不皈依于上帝,无需许诺永恒责任。”
50年过去了,在美国,像凯鲁亚克那样横贯美国成为不少即将步入大学围墙的年轻人的成年礼,他们18岁;而慢慢老去的婴儿潮一代也重新踏上了年轻时候的路途,50多岁的体形让这段旅程不那么舒服,也许开着高级房车更现实;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作了LP,搭乘“灰狗”,想象着50年前凯鲁亚克们的荒唐事——现在也只有想象的份了。
《在路上》在中国卖得很好,但更多人只是为其盛名所吸引,它是一个接头暗号
只是有点难以想象的是,十多年来,《在路上》连同凯鲁亚克的其他作品在中国也会吸引大批忠实读者。去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的《在路上》成为这家出版社最畅销的出版物,10个月来累计卖出18万本。那部遗失了近半个世纪,前年才找到的剧本《垮掉的一代》,其中文版在上海书展一推出就让不少稚嫩的中学生成了这部晦涩剧本的主要购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瓜分了凯鲁亚克大部分作品的中文版,两家出版社都对这些其实并不好读的文学作品信心十足。
当我10年前读到《在路上》的时候,吸引我的是小说中大胆的性描写和各种药物带来的奇妙体验,小说到底说了什么,其实并不在意,那时我也18岁,也曾经想过是否有必要在进入大学前疯狂地上路。经过10年各类文字图像的大胆轰炸,《在路上》实在已经不够“前卫”,像凯鲁亚克他们那种旅行我已经消受不起,即使那些死忠的背包客朋友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只为上路而上路——一路拍了哪些好风光、遇到多少次艳遇,这才是饭后的重要谈资。
我们的旅行、我们的所谓一点点叛逆,也许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都毫无关联,那《在路上》为何还能在远离洛维尔的中国畅销10多年?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许确实有那么多人着迷于凯鲁亚克和《在路上》的魅力,并在内心渴望像凯鲁亚克和卡萨迪那样,“让我们一起走吧!”而更多的人可能只是为“垮掉的一代”和“凯鲁亚克”的盛名所吸引,“垮掉的一代”、《在路上》、凯鲁亚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阅读品位的标志,标榜“在路上”成为一种时尚和接头暗号,而真正能把并不算薄的《在路上》看完的,其实屈指可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