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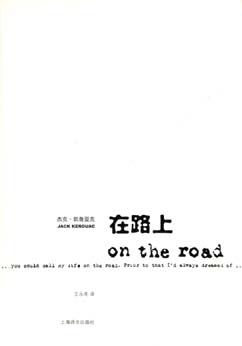 翻译家王永年于7月2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王永年精通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勤于翻译,译著等身,《欧·亨利小说全集》、《十日谈》、《约婚夫妇》,还有《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出自他的译笔。退休前,他作为新华社西班牙语的译审,工作了三十多年。 翻译家王永年于7月2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王永年精通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勤于翻译,译著等身,《欧·亨利小说全集》、《十日谈》、《约婚夫妇》,还有《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出自他的译笔。退休前,他作为新华社西班牙语的译审,工作了三十多年。
王永年女儿王绛称,父亲去世主要是因为患了肠梗阻,医生说也不能排除肠里面长肿瘤的可能性。“住院之前父亲已经骨折,身体不是很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因为身体比较虚弱,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只是在照顾他的八个月里,讲到自己的生平,他总是说,你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好好做学问,要终生学习。”在王绛的印象里,父亲在新华社上班的时候,为了多做一点文学的翻译工作,每天三四点钟就起来。“他去世的时候就是凌晨三点。我感觉,他是再也干不动了才去世的,他要休息了。”
因为王永年留下丰富的文学翻译遗产,赵德明、尹承东、赵振江等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纷纷对他的去世表示痛惜。赵德明表示,王永年是西语界的翻译大家,他在外语、中文、历史、文化上具有全方位的才学,他翻译的作品传神、忠实、精彩,文字也好,他的去世是西语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尹承东表示,王永年是地地道道的资深翻译家,他学问全面,治学严谨。西班牙语文学界对他的翻译水平、治学态度都很尊重。赵振江则认为,王永年可以被称为“翻译界的多面手”。他掌握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并能把原文吃透,这一点值得学习。“当下翻译界处于新老交替阶段,青黄不接。像王先生这样能翻译多个语种,并能同时涉及诗歌、小说翻译,且保证质量的译者是可敬的。”
学者止庵从读者的角度,谈到1980年代初,最早读博尔赫斯就是王永年先生翻译的译本。当时读得很入迷,被作者所吸引,惊叹小说还能这么写。博尔赫斯影响了很多中国作家和读者,很多中国作家都学习他的写法。王永年最早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博尔赫斯,他的翻译严谨,并能从中看到深厚的中文功底,他的译作是可以传世的。英美文学专家陆建德表示,欧·亨利的作品中国介绍得很早,20世纪初林纾就翻译过,对我国作家的创作影响也很大,王永年的翻译提供了一个现代版本。“听说他翻译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很吃惊,这本书年轻人很喜欢,他这样一个资深译者翻译的多是经典作品,要翻译嬉皮士文化的代表作,是一种挑战,他的勇气和精神令人钦佩。”
尽管因为翻译那些严肃高雅、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作品,王永年得到业界内外的推崇,但他却因为翻译看来不见得达到了这些标准的《在路上》,收获了更广泛的关注。出版人赵武平回忆说,请王永年重译《在路上》,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最注重的是“信”,这可能和他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有关。“以我看,译文的风格再明显,如果没有以准确为基础,就离原作比较远。王先生的翻译没有匠气。他的汉语修养很高,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
在赵武平看来,王永年之所以能具备如此高的翻译素养,主要在于他确实具有语言天赋,而语言天赋是一个好的翻译家最重要的素质。“王先生出身官宦家庭,父亲是民国云南高级官员。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受传统教育,长大后在圣约翰大学读的书,之后在新文艺出版社与王元化、张中晓合作,这些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生前接受采访时,王永年多次表示自己并不喜欢 《在路上》,但他还是花了十个月时间一点一点把它翻译完。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喜欢还要翻译?他表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不喜欢这样消极的小说,但可以介绍它是怎么回事。”
这颇能反映出王永年低调而达观的个人性情。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他与后来名声大噪的作家张爱玲是同学,但他并不因此刻意拔高张爱玲的形象。“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她跟我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她也像我们一样走中山公园。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她看不起人,我干吗要和她说话,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别以为她……她有时候考得不如我好。”又比如,有人问他为何翻译了如此多的文学作品,他想了半日,也只是诚实地说:“为了谋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武平认为,王永年在翻译界不是傅雷,不是李健吾,也不是杨绛。他是一个职业翻译家。“王先生经历过‘反右’,晚年坦承当时也有‘不由自主’的时候。但是他能直面这些经历,这体现了他骨子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翻译作品,在特殊年代里也有一些是‘完成任务’,有些他自己并不满意,但是他能实话实说。”
或许,王永年留给后世的,除了沉甸甸的文学翻译遗产,就是这种堪为典范的职业精神。他回忆自己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时,别人投来的稿,他都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都是长篇,比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天才》,一看就是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