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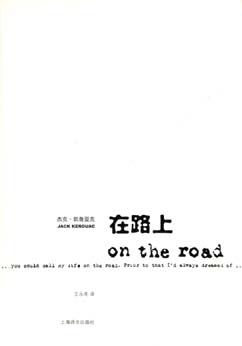 “垮掉的一代”用生命反抗被物质异化的工业社会 “垮掉的一代”用生命反抗被物质异化的工业社会
事出有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进入工业消费社会全盛时期,美国出现了这样一些人,赫伯特·亨克用“垮掉”(beat)这个词来描述他们。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晚期的黄金时期,许多人注意到了美国梦的一个个破产,同时,一个高度异化的后工业社会诞生。那时“垮掉”的青年们开始尝试他们自以为的生活方式,诸多的原因导致他们混迹于社会的低层——黑色或灰色的地带。当他们目睹了表面辉煌的高度异化的工业社会底层真相后,狂躁、放纵,他们对真实的美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垮掉的一代”流浪、吸毒、性放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挥霍着生命和青春,因为强烈排斥资本工业生活而穷困潦倒。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谁也救不了他们。艾伦·金斯堡在《我的黎明俪歌》中写到“我二十几岁的青春/在市场待价而沽/在办公室里昏厥/在打字机上痛哭——每星期六 任谁/都可以狂饮我的血库/这是我的一部分/算不上犯罪”,任何身处工业社会的人都深知这种生活的真相,作为资本机器的一部分,你无法脱离这个社会化的生存。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谁也不去考虑这样地狱般反人性生活的意义。
归根到底,“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敏感的人,有敏感脆弱的心,他们并不强大,他们愤怒和绝望是因为爱,他们用生命做赌注,抵抗压抑的被疯狂的物质异化的工业社会,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用艾伦·金斯堡的话说,他们属于“被疯狂毁灭的一代”(《嚎叫》),在垮掉的一代“垮掉”之前,他们已经彻底地形成了一个非常另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区别于主流的美国价值。但自然,对抗是艰难的。
《在路上》被称作是垮掉一代主要成员的自传,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凯鲁亚克的坦然诚实。这本书是真实的,你在阅读的时候分明能感受到这一点。新版的《在路上》中有安·查特斯冗长的导言,基本上说明了《在路上》的成书过程,也说明了作者的基本情况。
早于本书几年前开始选择在美国境内流浪的凯鲁亚克当时尚未成名,与众多的美国财富冒险故事相反,凯鲁亚克用穷困潦倒冒险,试图成功逃避一贯的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资本工业机器窒息下的美国青年新生活路子。《在路上》的成功也直观地印证了当时以至其后美国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心理需求,这种后来被称为“背包”的生活方式被西方世界的大部分青年人所接受和选择。
应该说,“垮掉的一代”以他们的方式强烈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国文化,这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反动,在典型的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成为青年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众所周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形,当人们回顾性和大麻这些令人感到刺激的亚文化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它们作为鲜明的符号,在畸形的消费社会所传达出的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这是和强大的资本体系最为激烈的对抗,包括反战和民权运动。
“垮掉的一代”对生命进行自我反思
当然,许多人都意识到,即使在垮掉一代成员中,除了他们共同所拥有的诸如拒绝为资本消费体系效力、流浪、吸毒、身体放纵、同性恋、双性恋等等之外,他们的精神理念也不尽相同。如艾伦·金斯堡一贯的对社会猛烈狂放的批判,他诗歌中的血肉鲜活的疯癫状态。而凯鲁亚克则在自己的作品中回到了一种本质上脱离了文明窒息的消费都市的一种身心上的清澈。当然,在对工业和消费社会的批判这一点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垮掉一代的成员信奉禅宗,以期从这一东方宗教中获得身心的结果和内心的清澈宁静,他们中有的人毕生致力禅宗研究并选择相应的生活,比如斯奈德。
从某种意义上说,垮掉一代大部分成员都是有文化的人,不仅如此,他们拥有不可抑制的天才。而他们的企图也是明显的,就是反叛工业消费社会的中产价值观,如此而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早期进入大学,又自动离校或者被开除,他们选择的潦倒的流浪生活使他们接触到一个确切的地狱般的底层社会,如此鲜活、疯狂和苦难。他们不断地发现,并且进入这地狱世界,妓女, 毒品贩子,皮条客,黑社会,小偷,吸毒、酗酒,打架闹事,做苦力等。而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做出这种选择时的决心以及他们最终从这样一个世界里回到最真实深刻的人性的结果,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深刻的生命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