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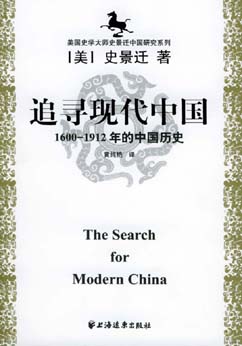 1962年2月,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一位三年级学生正在考虑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该通向何方。导师芮玛丽问他:“还想继续研究清初的历史吗?”学生答说:“想。”也许,恰恰是这次在私下场合里发生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决定了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此后40多年的研究走向。 1962年2月,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一位三年级学生正在考虑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该通向何方。导师芮玛丽问他:“还想继续研究清初的历史吗?”学生答说:“想。”也许,恰恰是这次在私下场合里发生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决定了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此后40多年的研究走向。
不管我们的目的是寻觅发源地,还是追溯发迹史,史景迁的清初情结是绕不过去的。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曹寅与康熙》(1966)讲的是康熙,他最近的著作《皇帝与秀才》(2001)讲的是雍正,几十载兜兜转转,他还是离不了这一时段。
假若我们可以将一维的时间铺展到二维的平面,假若我们可以将整个中国历史看作是一张中国舆图,那么从中心地带到边缘地区,应该依次是先秦、汉唐、明清、近现代。先秦也的确曾是汉学的中心,只要想想马伯乐的《中国古代史》只写到了秦朝这一事实,就什么都明白了。然而,事情总归要起变化。今天,当我们试图指出中国经济文化最活跃的区域时,首先想到的一定不是处于中心的河洛地区,而是想到边缘,想到上海,想到广东,汉学(尤其是海外史学)的势力消长亦未尝不是如此。海外史学的“虚中”现象是必然的,因为亲缘性具有决定作用——我们总是更注重与我们切身的,更注重当下,更注重眼前三尺,如果不是眼前三寸的话。海外史学的磁场中心始终是活生生的当代中国:他们研究过去的中国为的是搞懂现在的中国,那么,过去的什么东西看起来对了解现在的中国最有助益呢?显然,是刚刚过去的那段过去。
在现代与清初之间,走“Z”字
史景迁刚起步的时候,已经看准了当时的边缘。那时,清代还是边缘,就好像广州是中国的边缘。不过,边缘一直在推进着,后来广州都不算边缘了,深圳才是真正的边缘——边得没法更边了。在这最边的边缘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磁场,你想,本来在“次边缘”地带活动的史景迁会受到怎样的引力呢?事实上,他不断地屈从于这引力,但又不断地试图摆脱这引力,想回到他最初为自己设定的基点上来,守住当年他对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们循着时间顺序,谛视史景迁的著述表,就不难发现“边缘”与“次边缘”上展开的拉锯战。1966年,《曹寅与康熙》是典型的清初。紧接下来,第二本书《改变中国:1620年至1960年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就已经大幅度向近现代倾斜。可是,第三本书《康熙自画像》又缩回到清初来了,第四本小册子《王氏之死》仍在此地徘徊。第五本书《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则力破余地,“现代,太现代了”。第六本书《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再次转折,后撤到比清初更远的晚明。1988年的小册子《胡若望的疑问》同《王氏之死》一样,也在清初打转。1990年的第八本书《追寻现代中国》,题旨显豁,且是史景迁篇幅最巨的一部著作(中译本是腰斩过的上半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上三分之一身),用力皆在现代。文集《中国纵横》且不去管它,第十本书《“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则是一次“中间地带”的犹疑,既不是清初,也不属于现代。往后是与人合著的《中国世纪:百年图像史》,当然属于现代。1998年的第十二本书《“大汗之国”——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帝国》,在我看来是史景迁最没想法的一部:居然从马可波罗讲起。要知道,出了大清国的地界儿,那可就不是他的势力范围了。下面一部是《毛泽东》,再探现代。第十四本书,2001年的《皇帝与秀才》,重返祖居。史景迁的“Z”字形著述路线,无疑是一种焦灼的反映。在现代与清初之间,他有些疲于奔命。不过,你也可以说,就像在广州、深圳间跑生意的一样,这两个地方没有哪个他割舍得下。
从学者生命进程与旨趣迁移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回真向俗”的过程。“真”是目的单纯的学术研究,“俗”是眼光向下的现实关怀。自然,章太炎用的“真”与“俗”二字,容易让人怀疑有褒贬寓于其中。实际上,“真”倒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俗”,“俗”也可能是换一种表现的“真”,其间的隐微幽曲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被人推尊为“史学大师”的史景迁,处在那样一个地位上,恐怕不得不对当下现实作出回应——虽然在单纯的读者看来,历史是历史,当下是当下,再明白不过了。
来自番邦的地图绘制员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史景迁也算是一个地图绘制员的话,那他绘出的中国远非全貌,传统的中心地带被省略了,留给旁人去画。他画的应该多少类似于一张广东省地图,一张边缘的、但绝非不重要的地图。我宁可管他的oeuvre呈现出来的这一幅叫作“史氏皇清舆图”。为什么非要加上“史氏”不可呢?因为他绘出的地图难免与我们手头上的有出入,这种出入,与其说是地形学上的,不如说是人文地理学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