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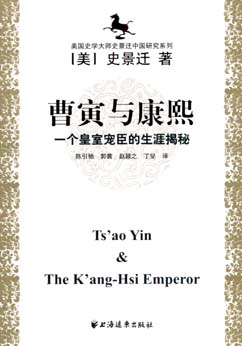 作为一个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名字有着一种格外的魅力。近日他在北京举办的四场活动,场场人满为患,包括3月9日下午,在中央美术学院进行的这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文化沙龙。美术馆不大的报告厅里坐满了人,连过道上临时摆放的方形纸凳子也被占满。其中慕名而来的还有作家王蒙、诗人西川、历史学者李零等文化名人。 作为一个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名字有着一种格外的魅力。近日他在北京举办的四场活动,场场人满为患,包括3月9日下午,在中央美术学院进行的这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文化沙龙。美术馆不大的报告厅里坐满了人,连过道上临时摆放的方形纸凳子也被占满。其中慕名而来的还有作家王蒙、诗人西川、历史学者李零等文化名人。
或许是因为有妻子金安平和学生郑培凯的陪伴,与前两天在北京大学纯粹讲述笔下的中国历史不同,这一次史景迁更多地分享了自己与中国历史的渊源与趣事,以及那些对历史的观察和研究结果。
康熙是博士论文题
78岁高龄的史景迁并未像之前那样穿西装、打领带。“我希望今天的讲座有一个轻松的氛围。”他的举手投足都十分轻缓,说话声音也小,外加英国口音,有时候很难完全听清他讲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英国人,光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就让人觉得很有趣。23岁那年,史景迁在剑桥大学毕业后成了耶鲁大学的交换生,来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学习过汉语,只是在临出发前把自己想要学的东西写下来,其中就有一个名词“中国”。
但说起他与中国历史的渊源,恐怕就要追溯到童年。“我6岁时就翻看了一本艺术史的画册,里面就有关于中国艺术的部分。二战期间,我觉得中国是英雄的形象。透过这些画册,我了解了历史中的中国,对中国史的感情也由此而生。”他笑着说。这种冥冥之中的缘分,一直持续到今天。
上世纪60年代,在耶鲁大学学习中国历史的史景迁正赶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时,美国对中国产生了强烈兴趣,特别是在语言方面。
史景迁当时的导师是芮沃寿与芮玛丽,虽然二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不同(前者主要研究佛教,后者则专注于近代史),但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文言文、繁体字,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但当时我很难决定研究什么题目。后来芮玛丽向我介绍了房兆楹先生,房先生提醒我,要去观察中国历史中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房兆楹的影响下,史景迁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主题锁定在了康熙身上。
1965年,他以一篇题为《曹寅与康熙皇帝》的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为了写这篇论文,他对康熙和18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藉房兆楹先生之力,他还得以在台湾接触到一批十分珍贵的史料,而这批史料都是国民党撤退时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带出的。
“我看到了许多康熙亲自批示的奏折,从中了解到一些康熙的个人想法,作为历史人物,他的个人形象也能通过这些细枝末节而变得鲜活。”他说。
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史景迁不止一次在现场表示自己对康熙皇帝的喜爱。
就在上周五晚的北大演讲中,他还曾说自己“最愿意和康熙交朋友”,因为“他相当灵活,他爱钱但并不如命,他爱他的60个孩子组成的大家庭,他有帝国设计,他也是首个一对一接见西方人的皇帝,甚至还学了一点外语”。
“有一次在翻阅康熙御批真迹的时候,他发现康熙把‘密’字写成了蜜蜂的‘蜜’。”妻子金安平说。对此,史景迁调侃道,因为康熙和他都是从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汉文,这让他对这位皇帝有同病相怜之感。
或许是源于这份“康熙”情结,史景迁在论文完成的第二年写就了自己的第一部同名著作《曹寅与康熙》。该书勾勒的情节始于曹寅祖父所处的满人巩固天下时期,止于乾隆时期曹寅孙子的时代。有鉴于曹寅是满人统治者的包衣奴仆,他们的故事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与表现的变易。尽管所触及的范围不能期望可以尽诉满人统治头一百年的种种变迁,但至少可以呈现它缤纷的样貌。
“您第二本书——《改变中国》的写作初衷是什么?”面对提问,史景迁回答道,从晚明利玛窦来华到1949年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建设,外国人试图改变近代中国的努力从未间断,其结果或好或坏,也许他们都是出于好心,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些人都是带着自身的幻想或是本国固有的经验来改造中国。“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情感上的偏倚。这其中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史景迁的写作一条线是写中国本地的历史,比如康熙、张岱;一条线是研究史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还有一些很早到欧洲去的中国人的故事,比如这次他带来的新书《胡若望的疑问》。
“书写历史,从不同的层面观察可以得到不同的想法,就好比彩虹,变化角度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色彩。”史景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