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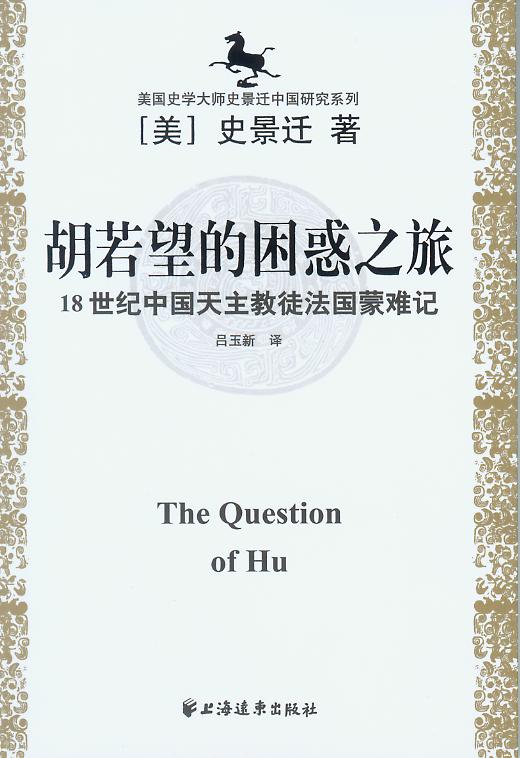 妙笔生花的史景迁,讲话却低沉严肃,甚至声调都少有起伏。他语速缓慢,对话中没有机敏的应对,多是四平八稳的陈述,“可能”、“不一定”、“某种程度上”是常用词,显示出学者特有的严谨和“无聊”。当我请他在一本2002年台湾版的《毛泽东》上签名,他也婉拒了,因为年代较早,他不记得曾有这个版本,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审校过这一版的翻译。近几年广西师大理想国陆续出版“史景迁作品系列”,翻译方面史景迁都和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他的大弟子郑培凯共同讨论过。 妙笔生花的史景迁,讲话却低沉严肃,甚至声调都少有起伏。他语速缓慢,对话中没有机敏的应对,多是四平八稳的陈述,“可能”、“不一定”、“某种程度上”是常用词,显示出学者特有的严谨和“无聊”。当我请他在一本2002年台湾版的《毛泽东》上签名,他也婉拒了,因为年代较早,他不记得曾有这个版本,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审校过这一版的翻译。近几年广西师大理想国陆续出版“史景迁作品系列”,翻译方面史景迁都和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他的大弟子郑培凯共同讨论过。
这无疑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反驳了一些人对他的诟病。由于文笔好、会讲故事还畅销,史景迁的历史研究一度被说成是“野路子”,甚至被质疑书中材料的来历。事实上他为每一个章节都提供非常详尽的注解,而且也很难想象一个连说话都那么深思熟虑的人,会在著书立说的时候犯下不问出处、胡乱想象的错误。史景迁曾师从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Wright)和中国明清史权威房兆楹,他的中文名就是房兆楹取的,意思很明白,“景仰司马迁”。他说:“如果碰到司马迁,我可能会脸红结巴,想邀他一起去喝啤酒,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家。”
尽管与孔飞力(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并称“美国汉学三杰”,史景迁更多是活跃在史学界而不是汉学界,他做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就是整个美国历史学界的领袖。从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开始,史景迁的研究看似没有“专攻”,实际上环环相扣:《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和《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分别是对一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和最弱势的普通妇女的特写,反映了一个强大帝国中两个极端的生活;《胡若望的疑问》和《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当西方遇到东方》则是早期中西方交流(主要是宗教促成的往来)的两个个案;《大汗之国》综观西方人想象中国的历程……他总是在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接触到了另一个课题的材料,有时候,很好的材料突然唾手可得,他不可能不写。比如 1963 年在台湾,他进入当时还设在台中的故宫文物仓库,有机会将康熙朱批的奏折拿在手里细看,而这些奏折中有他写给内务府曹寅的,于是曹寅与康熙的研究课题便形成了。
这次来到中国,史景迁对自己受欢迎的程度非常震惊。学生们踏破门槛要听他一场演讲,媒体也追着不放,他不喜欢接受采访,但最终同意分别给北京、上海两家媒体各半小时。3 月 24 日在复旦大学的最后一场演讲,主办方吸取北大讲座时人满为患的教训,要求凭票入场,但是领票那天的场面也相当火爆。最终,“主会场”之外,学校另开一间教室做视频现场直播,这间教室也基本上坐满了。复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甚至将史景迁此次中国行与 20 世纪早期杜威、泰戈尔等人来华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和80年代末在北京遭受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史景迁如今受到如此追捧,很可能恰好印证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教科书不可信了,《百家讲坛》一类的普及类节目讲者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总体上讲得不够深入,而史景迁代表了一种专业程度高、可信赖的,同时又是新鲜的讲述方式。尽管这种讲述不足以重新构建一个系统性的历史框架,但至少为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读者提供了重新审视的角度。
相对来说,生活中的史景迁是个更有趣的人,他和同为历史学者的夫人金安平都喜欢花草,在美国的住处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园。这次他们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和上海4个城市,除博物馆之外,杜甫草堂是最令夫妇俩兴奋的地方。在郑培凯看来,只有“幸福”这个词可以形容他们的生活。
B=《外滩画报》
S=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历史从来没有完成过
B:今年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第 150 年,就从这个话题谈起吧。近些年来,国内对这一运动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逆转。你写完《太平天国》已经 20 年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产生?
S: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不过我写作的时候,不光查了中文文献,也尽可能地查看了英语资料,试图发现更多信息。虽然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已经非常多了,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比如一些外国学者并不仅仅把它看成农民起义,他们认为太平天国代表了一种对社会转型的思考。我真的了解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包括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其他领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声明他们想要干什么。也许我对太平天国是有一点同情的,因为在那之后,是非常残酷暴力的一个世纪。
B:你在书里没有明确地提出你的价值判断,但是你有价值判断吗?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去年在台湾出版了,你看过吗?
S:我不是有意让我的书具有批判性或缺少批判性,但是你讲故事的方式,你分析不同人物的方式,对我来说就是臧否人物的方式,如果别人想在其中找到我的价值评价的话,其实已经可以找到了。史蒂芬是我在耶鲁的学生,写的大多是太平天国在湖南的事情,这是个有启发性的好故事,带来了新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