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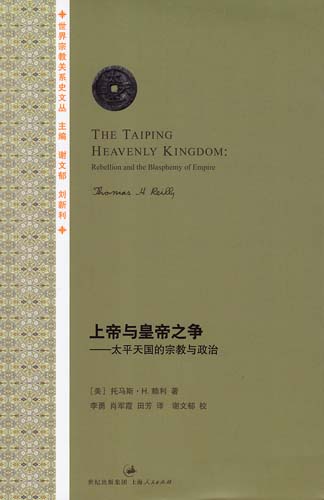 看连续剧《水浒传》,到晁盖曾头市中箭归天这一段,晁盖卧床不起,宋江、吴用守候在榻边,晁盖翕动着嘴唇问宋江:有没有考虑过山寨的未来?你不是念念不忘招安?宋江双眉紧锁,良久无言,起身独自走到门外。 看连续剧《水浒传》,到晁盖曾头市中箭归天这一段,晁盖卧床不起,宋江、吴用守候在榻边,晁盖翕动着嘴唇问宋江:有没有考虑过山寨的未来?你不是念念不忘招安?宋江双眉紧锁,良久无言,起身独自走到门外。
宋江诸人后来还是受了招安,人或以为梁山水泊的悲剧命运系由此注定,对宋江的责咎,基本也是从这里来的。显然,这种看法没有换位替当事人着想。反抗可不是多么浪漫的事,诚如剧中吴用所说:若不走招安一条路,山寨到头来也逃不脱被围歼的命运。更要紧的是,对于代代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宋江来说,赵宋朝廷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他没有理由去反对这个结束了五代纷争、恢复了隋唐时代汉人统治中原格局的王朝,尤其是在北方有异族兴起之时,忠于赵宋外御其侮,这样的大计是没有疑问的。
说到底,汉人反汉人政府合法性不足,只能得到有限的支持。倘若晁盖宋江们生在清朝,梁山泊的手脚就可以放得更开。
在洪秀全、冯云山们成立拜上帝会、谋划起义时,他们就没有纠结过“合法性”的问题。洪秀全曾说:“复明似是而非,既光复河山,自当另建新朝。”“自当”二字十分笃定,想一步到位,都不考虑借明朝来聚敛人心。有分析说,洪秀全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的姓氏恰好跨界,既可代表明太祖年号“洪武”,又与三合会公用的姓氏“洪”相同,还跟《旧约》里写到的上帝淹了世人的“洪水”有字面上关联。三者结合,洪秀全就认为自己身负天职了。当然,三者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与《圣经》及上帝、耶稣的联系。
洪秀全靠着宗教聚敛人心,两千年帝制那么多起义领袖,要数他最善用宗教。吕思勉说:“宗教本为结合下层社会,以谋革命的工具。历代借此号召的,都不过与恶政治反抗,或者带些均贫富的思想,到异族入据后,就含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了。”可是,一般的视线多集中在拜上帝教的荒谬上,因为这一点最是昭彰。洪秀全对《圣经》的核心概念一知半解,他涂改《圣经》文本为己所用。史景迁写《太平天国》,满以为他会像写《康熙》那样解析历史人物的内心,实际上这本书通篇读下来,“天王”基本没说过几句人话,不是在布道,就是在下“谕旨”,要不就是写大多为七言的打油诗——在在都表现了这场运动的荒诞不经。
洪秀全对基督教最大的曲解,据史景迁所写,在于歪曲“三位一体”,把圣父、圣子、圣灵掰开了用。理解“三位一体”超越了人类之逻辑,本就艰难,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洪秀全把他所援用和阐释的基督教降格为那种类似关亡巫术的东西,充满了灵魂附体和走火入魔的行为。洪秀全自称耶稣(天兄)之弟,东王杨秀清代天兄说话,西王萧朝贵代天父说话,萧战死后,上帝就经常“降凡”,临在杨秀清身上。这是巫术,还不是通灵,等到洪秀全被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欺压到无法容忍了,内讧爆发,管你是什么神人,世俗的刀剑血光解决一切。待日后太平天国烟消云散,这一切更是被打成了欺世的骗局。
我们在史景迁的《太平天国》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骗局,或者说闹剧。当洪秀全求教过的传教士罗孝全抵达天京时,他曾想矫正洪的种种宗教谬见,可是那时的太平军已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本土化仪式,而且战事吃紧。史景迁写道,罗孝全随便挑了一个士兵来问:“何为圣灵?”答曰:“东王。”这回答说明了一切。
如果不是掺和了宗教因素在里面,太平天国之反清的民族主义性质会更纯明一些,但是,洪秀全这个浑身上下极少半点军事家或政治家痕迹的人(至少在史景迁书中是如此),究竟能否像方腊那样“播乱”江南,就不好说了。有学者也试图以正面的态度来理解太平天国在宗教上的贡献。例如托马斯·赖利在《上帝与皇帝之争》中指陈,其他汉学家多不肯把洪秀全所为当作宗教事来严肃看待:“好像太平天国对基督教观念的坚持,对这场起义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似的。”基督教文献,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文献都大大忽略太平天国运动,传教士们都不重视太平遗产。赖利说,这种认识太过傲慢了,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大举印行《圣经》中译本(据他判断,这个译本是1823年由新教徒罗伯特·马礼逊翻译的),这是事实;此外,洪秀全举事前“很可能”已读过《圣经》,是直接受其影响,而不是《劝世良言》这种断章取义的二手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