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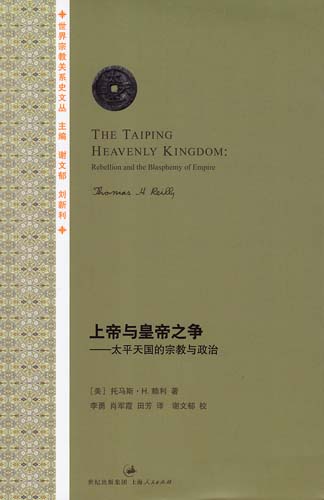 2011年岁杪,总觉得还有某个历史大事件没有大张旗鼓地纪念。直待看到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与托马斯·H.赖利的《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这才恍然大悟,2011年恰是金田起义一百六十周年,也是逢十的大年头。 2011年岁杪,总觉得还有某个历史大事件没有大张旗鼓地纪念。直待看到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与托马斯·H.赖利的《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这才恍然大悟,2011年恰是金田起义一百六十周年,也是逢十的大年头。
毛泽东曾历数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把这种农民的反抗运动,赞扬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象征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与象征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分别是八大浮雕之一。去年,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继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以后,以“最忠实的继承者”的身份隆重纪念其一百周年。然而,与前两个事件的高调纪念相比,对太平天国的纪念简直可以说是不着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有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说,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各居其一。按史景迁的说法,“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页5),如今同为逢十之年,纪念第三次革命高潮轰轰烈烈,对第一次革命高潮却少语寡言,未免让人有厚此薄彼之感。
无论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从罗尔纲到陶短房,从简又文到唐德刚,读书界不难找到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去年出版的两种,未见得是最佳作品。当然,如果你觉得“学术著作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不妨去读史景迁妙笔生花的《太平天国》。赖利表扬史景迁“以戏剧性的方式聚焦了洪秀全这个人,写下了一部生动感人的记叙”,但潜台词只是肯定其可读性,对它的深度似乎并不以为然。赖利自称他的研究“试图建构一个更广阔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页15),认为洪秀全发动的“是一场深刻的转变意识形态的革命”(页19)。这一说法,与毛泽东把洪秀全、孙中山列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落脚点上有那么一点契合。赖利一厢情愿地把太平天国运动诠释成基督教本土化过程的顶点,进而对“太平基督教”(即“拜上帝会”)不吝赞词,但读完其书,却感到他对这段历史颇有错判与误读。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学界往往纠结于“叛乱”与“革命”的定性。史家立场决定史实表述,誉之者颂其为民族革命(例如萧一山),阶级革命(例如罗尔纲);钱穆《国史大纲》称之“洪杨之乱”,《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称《晚清史》)称之为“太平军叛乱”。与其急于正名,不如首先征实,即确定这场运动最深层的动因与主要的参与者。
鸦片战争后,清帝国被动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种在坚船利炮威逼下的被迫开放,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妨说,正是鸦片战争,为太平天国运动种下了外部的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不久,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指出,“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对业已席卷中国南部的巨大风暴,马克思在揭示其“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的内因时,也深刻指明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破坏。
然而,正如唐德刚所说,在中国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是历史的“必然”,晚清历史蹒跚走到太平天国时,已进入“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当然,前述外因不仅缩短了这轮周期性,也加剧了内乱的惨烈度)。
整个社会的严重不公,官僚政治的全面衰败,官员道德的普遍沦丧,虽是历次王朝危机的共性,在鸦片战争前后十年间却于此为烈。早在洪秀全闹事的十二年前,素称富庶的东南地区,经贪官污吏层层加码,原先规定缴入国库的三升税米竟激增到一斗,愤激的农民无以卒岁,只得杀了耕牛另找出路。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吟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由于鸦片战争,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经济遭受深度的摧残,另一方面,为偿还赔款,头会箕敛变本加厉,贪污腐败与时俱进。及至1850年,连曾国藩都承认:“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也难怪起事民众在文告中抗议:“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据官方报告,金田起义前,杀官绅、占城池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广西七府一州。道光状元龙启瑞描述当时局势道:“如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