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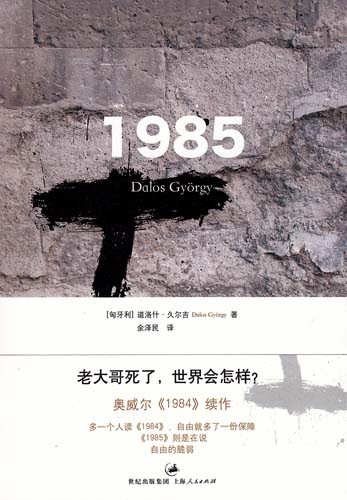 余泽民,1964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赴匈牙利定居至今。 余泽民,1964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赴匈牙利定居至今。
余泽民的文学道路正是俗语“迷失在翻译中”的反面。通过翻译,他找回了迷失的人生。
他就这样为自己写,为自己译着,直到凯尔泰斯获奖、母亲说“我儿子能译”的那一天。
2007年,余泽民前往柏林,拜晤长居于此的大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随行带着自己翻译的四本凯尔泰斯作品。作家先请他喝咖啡,后来开了一瓶酒,又留他吃午饭,聊了四个小时。临走时,将近八十岁的凯尔泰斯拥抱他三次,对他说:“所有翻译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亲人。”
余泽民闻之大为感动,当场落泪。
这位匈牙利老先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标记。2002年10月,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出版商开始争夺版权,并多方寻找匈语译者。余泽民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立刻宣布“我儿子能译”。但周围没人信她,因为都知道泽民学医出身,既没有专业的匈语背景,也没有专业的文学背景。
北京的街坊们没有说错。1991年年底,泽民坐了十天十夜的火车,穿过俄乡来到布达佩斯的时候,一句匈语也不会。此后三年,“我几乎没用母语说过话,偶尔给父母挂长途,心里都会紧张得要命,拨号前先在电话旁放一只手表,压一张字条,上边写好想说的话。”2006年,他对《文学界》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患了语言功能分裂症。”
那个时候异乡人的孤独是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的:手机难得一见,互联网远未普及,更没有五花八门的即时通讯或视频通话软件。1992年春天,余泽民被琼格拉德州移民局认定为“一个非法行医、与黑社会勾结的不受欢迎的人”,失掉了合法的居留身份。“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自己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地心惊肉跳。”泽民说,“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体会到饿的滋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这段艰困的时期,多亏了友谊、阅读和写作,让他抵抗着孤独,但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被语言分裂。他使用三种很少相交的语言:听和说用匈语,阅读用英语,汉语则用来写作。“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的唯一途径,匈语阅读则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内容。”他说,“我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以周围人难以理喻的激情写,并在这种执拗、孤独的写作中,体验到了近乎高潮的快感。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是:用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语言尽可能贴切地表述只有自己才能看到、听到、感到的东西。十年里,我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但是读者只有一个,就是自己。”
终于熬到第一个贵人出现。1999年,匈牙利作家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拉斯洛前往中国采访,泽民一路陪同翻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走了十几个城市。
回到匈牙利后,有人送了他一本新出的克劳斯瑙霍尔考伊小说集,他就这样偶然读起了匈语小说,刚开始十个字里有九个不认识,差不多每个字都要查字典。他后来合计,反正查也查了,不如干脆练练翻译。于是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译出了第一个短篇,约有八九千汉字,译完以后才听人说起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是当代匈牙利作家里文字最难懂的,很多匈牙利人都读不懂。泽民因此生出了信心,进书店看到短篇集就拿过来,读五页,如果觉得行,就买回家,边读边译,权当练笔。事后回想起来,他说自己虽然不信宗教,但“总觉得某种力量在推动你,安排你”。
他就这样为自己写,为自己译着,直到凯尔泰斯获奖、母亲说“我儿子能译”的那一天。
他说他喜欢匈牙利,喜欢上了匈牙利文学和匈牙利的作家,其中有一位艾斯特哈兹·彼得,像他一样留着一头疯狂的长发。
《英国旗》是余泽民翻译的第一本,也是最难的一本凯尔泰斯的作品。翻译界和出版社对他一无所知,感觉没底,所以老追着他要看样章,他自己也没底,觉得这本书太难读了,生怕出版社看了几十页打退堂鼓,所以硬是不给样章,直到合同规定的交稿时间到了,才交出整本译稿。泽民说,当年轻的编辑朱燕回信告诉他,从未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这对读者也是一个挑战的时候,他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放下了。
为了赶时间,出版社只给了他一年半来翻译四本书,逼使泽民完全投入其中,“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机遇,”于是除了翻译什么也不做,玩命地、疯狂地工作,以至于一两个月才有时间洗上一回澡。
从2003年到2006年,余泽民译、冒福寿审校的四本凯尔泰斯作品——《另一个人》《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和《英国旗》陆续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没有想到国内一下子对我很认可,觉得文字确实挺好的。”泽民说。
今年9月13日,他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医学部,面对满堂昔日的师友和年轻的学生,回忆自己从匈牙利外省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赤脚医生,到今天坐在讲台上的文学翻译家这二十三年的历程。“我开始翻译,完全就是这么一个机遇,但有的时候你有目的地做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也做不成。?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