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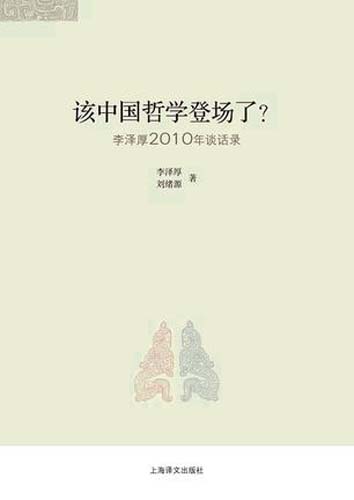 李泽厚先生是当今中国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席教授,其重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中国思想史论》等。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这套文集由古希腊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经典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李泽厚先生是当今中国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德国图宾根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席教授,其重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中国思想史论》等。2010年2月,美国最权威的世界性古今文艺理论选集《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第二版收录了李泽厚《美学四讲》“艺术”篇中的第二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这套文集由古希腊柏拉图的论著选起,一直选到当代。李泽厚是进入这套经典文论选的第一位中国学人。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去年推出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一书一年内连印四版,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去年夏天,趁定居美国的李先生回国之际,著名学者刘绪源再次与李先生作深度对谈。这次谈话的内容更为生动和丰富,是对李先生哲学思想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梳理。我们特请刘绪源先生选取长篇对话中的部分话题供本报刊发,与读者分享这位八旬老人的最新学术思想。
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哲学实力
刘绪源:在我们的上一本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你以前的文章中,你都强调了“度”的本体性。关于度,我当初曾产生过疑惑。我想,“度”应该是中国和西方都讲究的吧?做任何事,都不能失掉分寸,不然不会成功。西方科学技术那么发达,那就说明他们很讲究度,只要有哪一点不合度,立刻就不能成立,不会成功。为什么你觉得在中国思想中,“度”显得那么重要呢?是不是说,西方哲学与它们的科技是不同的,它们在很多时候会忽略“度”的重要性,从而走向某种极端?
李泽厚:不光西方科学要讲“度”,连动物的活动也要有“度”,否则没法生存。问题在于人类的“度”从哪里来,与动物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把它提升到哲学上。西方哲学的出发点是什么?是logos,它至少有两个解说即逻辑和语言,都是理性。逻辑推演不和现实直接发生关系,它的“度”便不突出。语言不讲度,我们上回说过,可以“胡言乱语”,话讲多了不会死人,所以可以走极端。只有外交辞令讲度,不然要损害甚至危及两国关系,引发战争。当然,语言、逻辑本身的独立发展有其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始终赞扬西方的“思辨的智慧”。但好些哲学家建造了一座座语言的迷宫,制造了许多深奥的概念、词汇,自迷迷人,于世无补,自己和追随者们却出不来了。我以为海德格尔晚年有此问题。
刘绪源:但你的“情本体”哲学也要用哲学语言来表述。
李泽厚:当然要用语言和哲学语言,但不一样,“情本体”不从逻各斯出发,而是从生存经验出发。我说过“两个本体”,这“两个本体”正如拙著《哲学纲要》用黑体字所标出的:“双本体又仍有先后”之分。这“先后”包含时间,更重要的是逻辑秩序。你虽然紧扣住“情本体”不放,我却总要从“度”、从“工具本体”讲起。首先是“工具本体”,有人根本没看清楚就批评说,“工具”是死物质,怎么能是“本体”?其实工具之所以叫工具,正因为它是在使用中,也就是海德格尔的“上手”,工具本体讲的正是人的生产-生活-生命。第二个“心理本体”即情理结构。这两个本体就是我反复说过的外在人文和内在人性,外在的礼(义)和内在的乐(仁)。这讲法不是以中国古代的种种文献或各家学说概念为依据和出发点,而首先是以中华民族这个古老存在实体的实践活动为依据和出发点。中国五千年的生存经验——再往上推,可以有八千年,这样的体量和这样漫长的时间,我称之为十三亿人的“巨大时空实体”,它的“生存的智慧”才是今日哲学最重要的依据,这才是我的哲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基础。我常常想,为什么其他古老文明——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河文明以及玛雅、印加都一一消亡了?古希腊、罗马如果不是经过阿拉伯文明的承续,也不会传下来。但中华文明八千年不断,铸造了这么大的一个时空实体,其中所包含的生存智慧,这才是中国哲学登场世界的真正实力和基础。
人类与动物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李泽厚:现代基因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近亲是黑猩猩。人与黑猩猩的差别很小,有98%的基因是相同的;相反,黑猩猩与大猩猩之间的差别却更大。但你看看现在人类,又是飞机又是电脑,谁会把人和黑猩猩看成同类,反而把黑猩猩和大猩猩看作异类呢?到底哪个差别大?不管是黑猩猩还是大猩猩,能造个房子让我们这样坐着喝茶吗?可见这差异并非基因造成,人类并非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自己把自己建立起来的,人类不是靠基因变化而是在长期使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人从原始人类到现在,基因未有大变,但差异不是很大甚至极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