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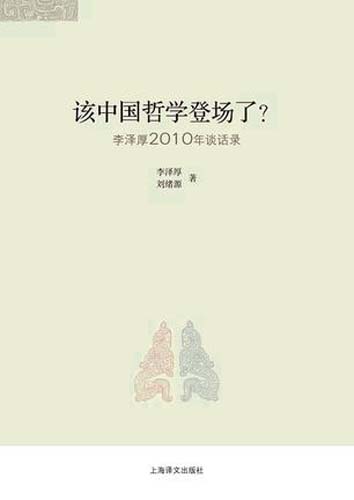 李泽厚与刘绪源二位先生的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去年4月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一年内连印四版,行销二万余册,受到读书界关注和热议。去夏刘绪源先生赴京又与李先生作了第二次对谈,对李泽厚哲学思路和最新思考作了进一步梳理,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将编为《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报现征得作者的同意,选摘部分内容刊出,以便读者先睹为快。——编 者 李泽厚与刘绪源二位先生的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去年4月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一年内连印四版,行销二万余册,受到读书界关注和热议。去夏刘绪源先生赴京又与李先生作了第二次对谈,对李泽厚哲学思路和最新思考作了进一步梳理,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将编为《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报现征得作者的同意,选摘部分内容刊出,以便读者先睹为快。——编 者
四个“静悄悄”
刘:我们的上一本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出版后,读者对其中的第二、第三章很感兴趣,你在那里谈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有些本来不喜欢理论的年轻朋友也爱看,他们大多读过《美的历程》,是把对话当你的传记看的。这次你也谈一点自己的故事吧。你的生平应该就是“珍惜、眷恋、感伤、了悟”的经历,从你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忧惧,到现在的“为人类”而活,也可说是“寻求意义”的一生。
李:我没有那么多故事,一生简单平凡,“书就是人,人就是书”,上次说了。我还说过,我有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静悄悄地读——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我的任何书印数不少于一万册,读者都是一般的青年、干部、教员、企业家、媒体人、军人,等等。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我有证据,例如各种报纸经常有他们谈读书的文章,说最近看了什么书之类,乱七八糟的书都有,就从没发现有谁在读我的书(大笑)。我的书既没宣传,也没炒作,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仍有人静悄悄地读,这非常之好。我非常得意。小时候父亲和我说以高下品德分四等人:“说了不做,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印象深刻,至今记得。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
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好些人以为我“很狂”,其实错了。
刘:还有两个“静悄悄”呢?
李:去年说过了:静悄悄地活——近十年,我的“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基本上执行了。十年中,也有两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座谈”,像是演讲,实际还是杂七杂八地回答问题。采访去年太多了一点,今年大都婉谢了。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或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昨天,我们的责编陈飞雪打电话来,问起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这可以谈谈。我对自然科学一直感兴趣。上次我也说过,中学里我理科成绩好。初中时的平面几何,一些习题很难,但我喜欢做。训练推理能力和想象力,比如划虚线。八十年代我写过文章,说初中要学好“没用”的平面几何,高中要开逻辑课,这很重要。据说现在把逻辑放在政治课里,这有点搞笑。因为逻辑如同语法一样,恰恰是没有阶级性的,这还是斯大林说的,毛泽东也说逻辑没阶级性,它是人类普遍的思维形式和规律,我真不懂为什么放在政治课里讲,与政治毫无关系嘛。
到大学,我专门去上数理逻辑课,练习做得很认真。那时系里分几个组,我差点到逻辑组去。欧阳中石是我同班同学,他就是学逻辑的,我们同时听过王宪钧的课。这是我1954年做的数理逻辑笔记(取出当年笔记),金岳霖的《逻辑》里所附的那些题目,我大部分都做过,经过严格的推理训练。我从不苦思冥想,但力求概念清晰,思想周密,大概与这有关,虽然自己并未感觉到这点。我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学好逻辑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很欠缺。
我与胡风案
刘:谈一下“反胡风”中的事吧,是否差点把你也卷进去?
李:我北大毕业,几经折腾,一个偶然,进了中国社科院。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挨了一通整。因我说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人,说路翎的小说极有才华,我欣赏胡风《七月》、《希望》、泥土社、蚂蚁社等等名称和封面设计,觉得不落俗套而坚实朴素,是鲁迅遗风,还有我买了胡风的《意见书》送人,等等。说我是“胡风分子”,整了一年。这中间,还把我带去参加执行枪毙前的“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为了吓唬我。但又怕我自杀,因为跟我同案的一个好朋友,非常好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自杀了。我才不会自杀呢。但逼我写了一大堆什么“我就是胡风,如何如何”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