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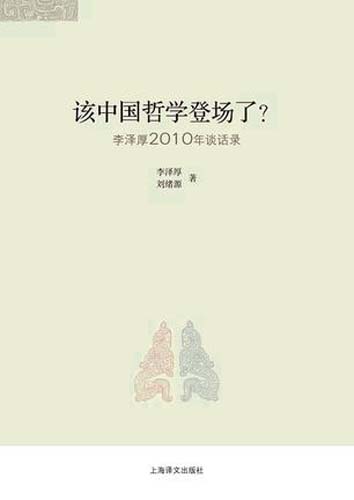 把中国哲学看作世界的希望,这在国内国外都已不新鲜,但是在西方哲学依然强盛的年代,这种思维包含的更多是对西方失望之后对东方单纯的期许。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哲学会登场,可它何时复兴,将以何种方式给迷失的世界以指引,对西方哲学是替代还是改造,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 把中国哲学看作世界的希望,这在国内国外都已不新鲜,但是在西方哲学依然强盛的年代,这种思维包含的更多是对西方失望之后对东方单纯的期许。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哲学会登场,可它何时复兴,将以何种方式给迷失的世界以指引,对西方哲学是替代还是改造,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这个问题,李泽厚先生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出手登场的时候了。”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一书中,他给出了很确定的回答。当今西方哲学和它引领的社会还是无法克服自身的困境,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李泽厚认为,化解危机必须在危机源头处就转向东方,和中国哲学接上头,一个“该”字把中国哲学的现身定格在了当下,并给出了明确的接入口,让人不得不兴奋。
李泽厚何以有如此结论?怀着对这位被媒体称为学贯中西、“中国屈指可数的原创型的思想家”的期待读完了这本书,但掩卷而思,却有诸多疑惑。
对于中国哲学登场的问题,李泽厚是从他的“情本体”论中延伸出的一个推断,之前也有提及,书中却没有新的论证和依据,其他问题,诸如如何登场,对西方哲学是替代还是改造,与之并存还是融合等等都语焉不详。他主要还是在围绕“情本体”论述中国哲学及思想登场的理由,总结起来不过两点:一是,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构筑了一套以思辨、理性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理论,情感被划归在艺术中和哲学隔开。但是随着启蒙运动兴起,这套理论中的绝对价值被质疑和抛弃,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平庸之时,西方哲学走向了反理性的极端,后现代哲学滑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不过人依然活着,如今科技已脱离人的控制成为人自身存在的威胁,使得未来更加不明朗,上帝之城的消失成为必须要填补的空白。二是,中国是没有西式哲学的,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西方那一套,只有广义的形而上学,中国人的思想是“由情入理,西方却是由理入情”,这种用血缘做基础,用人情纽带建立起来的对外人道主义和对内理想人格的模式,既不以理灭欲,以求绝对,也不以情排理,走向虚无,这就是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他认为这恰恰是可以和后现代哲学接上头的,正好排遣了西方哲学的迷茫和困惑。看来伴随中国的复兴,中国哲学必然也必须承担起它的使命。
由此,一破一立也就成立了,中国哲学的登场也就顺理成章。然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哲学本身。西学已破,那中学呢?李泽厚认为“情本体”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沉淀下来的,如今这种实践已经在它的发源地发生了巨变,如果只是在古书中取得文字上的解脱,那又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五四之后,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哲学发生了断裂,过往的文化热又是在反传统,其实中国还有多少传统可反呢?如果真正的哲学是在生活之中,那如今的生活中还有多少是中国真正的传统呢?
如果仅从学术层面赋予中国哲学登场的理由,那现实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础,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在西方经济模式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他所说的中国哲学可能在现实中已经很难寻觅了,结果很可能是,西学已破,中学难立,中国哲学如今的局面,登场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自身重建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