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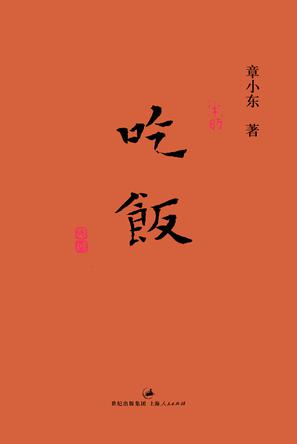 在海外的生涯中,我和李泽厚先生共同的最为亲近的年轻朋友,要数章小东(章靳以之女)和她的丈夫孔海立(孔罗荪之子)了。“关系”往往会影响评价,所以文学批评者最好不要和文学作者的关系过于紧密。不过,我们今天一起谈论小东的小说,第一原则还是严守文学的尊严,面对的是小说《吃饭》的文本,而不是友人章小东。小东这几年发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火烧经》(这个题目起得不错),已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推荐者是大家熟知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葛浩文与王德威。德威兄还特别作了一篇认真的序文,他衷心觉得小东的小说写得好。《吃饭》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我从马里兰剑梅处把小说打印稿带回科罗拉多时,先请泽厚兄阅读。他眼睛不太好,无法阅读文本。我把故事情节讲给他听,还给他读了一些段落。他听了之后说:“小东不简单,把海外的生活如实写下来。我还是喜欢这种现实主义的写法。” 在海外的生涯中,我和李泽厚先生共同的最为亲近的年轻朋友,要数章小东(章靳以之女)和她的丈夫孔海立(孔罗荪之子)了。“关系”往往会影响评价,所以文学批评者最好不要和文学作者的关系过于紧密。不过,我们今天一起谈论小东的小说,第一原则还是严守文学的尊严,面对的是小说《吃饭》的文本,而不是友人章小东。小东这几年发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火烧经》(这个题目起得不错),已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推荐者是大家熟知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葛浩文与王德威。德威兄还特别作了一篇认真的序文,他衷心觉得小东的小说写得好。《吃饭》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我从马里兰剑梅处把小说打印稿带回科罗拉多时,先请泽厚兄阅读。他眼睛不太好,无法阅读文本。我把故事情节讲给他听,还给他读了一些段落。他听了之后说:“小东不简单,把海外的生活如实写下来。我还是喜欢这种现实主义的写法。”
泽厚兄如此肯定小东的小说,还和小说的主题有关。小说干脆以“吃饭”命名,不怕人家讥讽“不雅”,文本与题目契合,整部小说写的全是吃饭的故事。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故事娓娓道来,不刻意雕琢,文笔质朴而干净,主题明晰而突出,写实写得让人忘记是小说,仿佛是一部生活笔记。这种文体,早已有人称作“纪实小说”。书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写了一段李泽厚的“吃饭哲学”:
吃饭? 我想起来著名美学家的“吃饭哲学”, 那位思想界的巨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冠上一个通俗的名字“吃饭哲学”,遭到不少假正经的学者们的讥讽。然而对我来说,反而还是“吃饭哲学”更加直接贴切。就好像台湾人把文雅的“如厕、方便、解手”等直接称为“放屎”一样,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吃饭实在是人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件大事,为了吃饭许多人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而我不也是违背了自己吗?想到这里有些感伤,看着酒杯里空空荡荡的清酒,嘴巴里泛起苦涩。
小东认同“吃饭哲学”的理念,但整部小说却一点也不理念。相反,这是一部最见生活血肉和生活气息的小说。读了之后,我们简直可以闻到包子的香味、牛排的焦味、土豆烧牛肉的美味,甚至可以看到萝卜黄瓜的雪白粉嫩,咸菜豌豆的碧绿生青。用王安忆的语言说,这叫做“生活的肌理”。章小东的《火烧经》写的是国内的生活,那是动荡的年月,也是连饭也吃不上的年月;而这一部《吃饭》,写的则是海外的生活,这是平常的岁月,也是寻找“饭碗”的岁月,然而,却又是找到饭碗却丢失了“吃饭味道”的岁月。小说这样结束:“我找到了吃饭,却丢失了味道,这是我在异乡的长梦里常常出现的味道,过去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我自己的味道。”年少的时候,在家乡上海,在父亲、母亲、外婆的温馨“卵翼”里吃饭,哪怕吃不饱,但饭菜样样都飘着亲情渗入的香味。那时虽然清贫,但不知道吃饭的艰难。出国之后,才知道在海外谋生很不简单。谋求吃饱饭,创造一个生活的前提,这是大事。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自由。没有这个前提,什么北美大地,什么温柔之乡,什么美妙理想,一切都不属于我。
读了小东的小说,我几乎经历了一次“惊醒”。原来,我的生活太舒适了。到了海外之后,虽说是漂泊,实际上却生活在自己的名声之下,在校园里自始至终拿一份薪俸,既无政治干扰,又无衣食之忧,简直是生活在一片乐土之上。读了《吃饭》,才重新想起了吃饭之难。连小东一家之难,也在阅读时才发觉。一个赤手空拳的文科留学生丈夫,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一个只会中文、不会英文的知识女子,三个人组成的家庭,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展开全新的生活。身边没有祖国,没有父母,没有兄弟亲人。在新的国度与新的规范中,仅靠丈夫的一点奖学金是不够的,必须自己去打工,但是刚刚出国时没有绿卡,打工不合法,一旦打工,移民局的官员随时都可以“带走”,而偷偷打工,每小时只有四美元的工资,为了这四美元,小东必须从B城转换两次公共汽车去D城,可是因为英语不好,在转车途中总是阴差阳错,充满迷失的恐惧,几乎像在历险。每天都有一份惊心动魄的“历险记”,本是上海上层社会的知识女性,到了美国,经历一番历险,方知吃饭的艰难。用这种艰难换来的“饭”自然不再香喷喷,而是充满苦味,而为了省钱,总是去抢购便宜货。小鸡降价(一只一点五美元),立即去抢购二十只;西瓜降价(九十九美分一个),赶紧去买二十个。结果最后几个烂在地毯上,吃的时候,不仅没有甜味,还有臭味。尝到饮食的苦味与臭味之后,才懂得什么叫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