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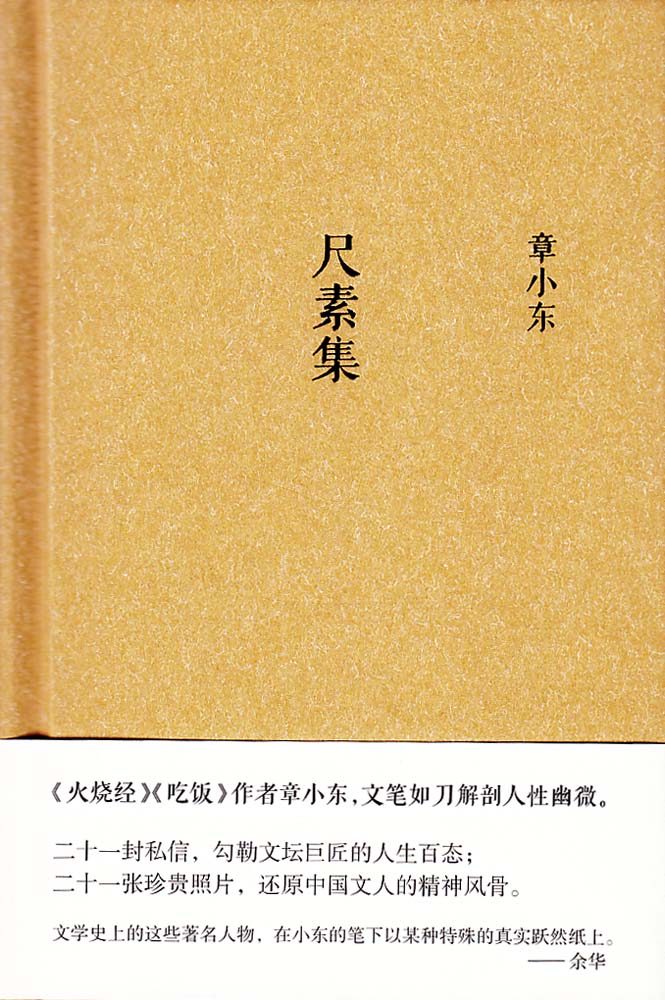 20多年前,章小东初到美国,舞文弄墨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小姐卷起袖子,帮厨、端盘,琢磨烧菜,只为求一口饭吃,“出门在外,最要紧的是吃饭。凡是可以和侬一起吃饭的人,就会是侬的朋友。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就不会是侬这个中国人的朋友。”母亲的叮嘱,让在外漂泊的她执着于吃饭,也在吃饭中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爱。20多年后,这些海外寻饭吃的故事被章小东写进小说《吃饭》——文字反复描摹下的烹制的热情和美食的流连,让她得以释放自己与故乡割不断的羁绊。 20多年前,章小东初到美国,舞文弄墨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小姐卷起袖子,帮厨、端盘,琢磨烧菜,只为求一口饭吃,“出门在外,最要紧的是吃饭。凡是可以和侬一起吃饭的人,就会是侬的朋友。假如连中国饭也不接受,就不会是侬这个中国人的朋友。”母亲的叮嘱,让在外漂泊的她执着于吃饭,也在吃饭中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和爱。20多年后,这些海外寻饭吃的故事被章小东写进小说《吃饭》——文字反复描摹下的烹制的热情和美食的流连,让她得以释放自己与故乡割不断的羁绊。
可是,吃饭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留在了文字里,却也只在文字里;这些年,章小东屡屡回国,寻访当年的记忆,可惜的是,曾经的味道再不能觅。接受采访时,她安静地坐着,望着窗外淮海路常熟路口的车水马龙,“对过老早是永隆食品商店,现在没有了,马路变宽了,不知道为什么,马路也变高了,人多了。我也老了。我出去是为了找饭碗,我写吃饭,现在饭碗找到了,回来味道没有了。”
从《吃饭》到《味道》
星期日:你的小说《吃饭》写的是美国的生活,但里边满满的是乡愁,是上海的味道;到了结尾,主人公东东回国,要找过去的味道,直奔云南路,买了一堆吃的回家,却发现“那些小菜变了,变得和老早不一样了,一点味道也没有。”
章小东: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在写的下一本书,就叫《味道》,我要把这个味道找回来。前些年,我看《舌尖上的中国》,有一天看到介绍扬州的小吃,包子什么的,我从没去过扬州,就想着一定要去。后来我和先生一起去,走了一路,看到了很多东西,也吃到了包子,扬州那个地方好,交通没那么发达,我在那边的时候就想,如果能让我住在这样一个过去的城市,我情愿放弃掉现在现代化带来的便利。所以我要写扬州的味道,扬州有个个园,里面有个永远的月亮,不管白天黑夜月亮都在那,这就像扬州的美食,永远在那里;可是我想到的是朱自清,他是扬州人,他爱吃,也写过吃,包括吃包子,但是扬州人朱自清是饿死的,我这个“味道“和“舌尖”可不一样,我会选文学家,我要花大力气去写他们。
星期日:味道找得回来吗?
章小东:我跟你说一篇已经写好了的、去苏州找味道的故事。90年代我去看望姨妈张充和,那时候她已经90多岁了,你知道我很会做菜的,我就给她做饭,她说很好吃,但是她说有一样东西她一直很想吃,再也没吃到过,叫“飞飞跳”。你想一个90多岁的人,出国5、60年里一直想的味道,我就希望能让她再吃到。我想这个名字会飞会跳,一定和鸡有关系,她说是的,是鸡的膀子和鸡的脚,用鸡的肠子缠一缠,再卤一卤,然后再放什么东西,好吃啊,香啊;那我说我做给你吃,结果做出来了,她尝一口,“太烂了,不好,不对”。于是我就去苏州找“飞飞跳”了,我走了很多路,做了很多调查,问了很多人,我几乎找到“飞飞跳”了,好像就在门口了。
星期日:《吃饭》里边,主人公东东在美国,做饭很能创新,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但是实际上,你要找的是过去的“味道”?
章小东:我是很老派的,口味是classic的,各方面都很传统,就是外国人说的中国女人,是一条直线的,从女儿到妈妈再到祖母;不像外国女人是一条横线,女孩,老婆,朋友,情人。我是很传统很传统的一个人,吃东西更是这样了,去北京吃烤鸭就吃全聚德的,其它创新的我都觉得难吃,所以我的北京“味道”就准备写鸭子;上海的天鹅阁,我在《吃饭》里边写到过的,我要去找到它,我还要写。这就是我寻找味道的故事。我出去是为了找饭碗,我写吃饭,我饭碗找到了,回来味道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