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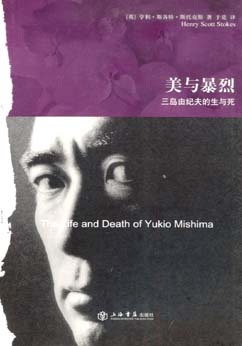 我第一次见到三岛由纪夫是在1966年4月18日,他的名字读起来短促有力——Mi-shi-ma。那是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他作为贵宾将在餐后发表演说。那时候,他正值四十一岁,风华正茂,是位已被公众认定必会荣膺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他的太太瑶子也随行出席。三岛夫妇落座于主席位,身旁坐的是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是当年的俱乐部主席。我的座位距离主桌还有点儿距离,但并不影响我对三岛君的观察:他身材瘦小,但体格结实,风姿凛冽,头发剪得极短,几乎是平头的造型。皮肤略显孱弱的苍白。当时我便想:毫无疑问,他过于操劳了,我知道他经常通宵写作。三岛的英语非常流利。瑶子夫人却刚好相反。她的身形也很瘦小,比丈夫年轻十岁,从相貌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瑶子夫人苗条纤弱,圆圆的脸庞,那时已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始终沉默寡言。 我第一次见到三岛由纪夫是在1966年4月18日,他的名字读起来短促有力——Mi-shi-ma。那是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他作为贵宾将在餐后发表演说。那时候,他正值四十一岁,风华正茂,是位已被公众认定必会荣膺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他的太太瑶子也随行出席。三岛夫妇落座于主席位,身旁坐的是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是当年的俱乐部主席。我的座位距离主桌还有点儿距离,但并不影响我对三岛君的观察:他身材瘦小,但体格结实,风姿凛冽,头发剪得极短,几乎是平头的造型。皮肤略显孱弱的苍白。当时我便想:毫无疑问,他过于操劳了,我知道他经常通宵写作。三岛的英语非常流利。瑶子夫人却刚好相反。她的身形也很瘦小,比丈夫年轻十岁,从相貌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瑶子夫人苗条纤弱,圆圆的脸庞,那时已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始终沉默寡言。
是夜,罗德里克先致敬词,简略讲述了三岛由纪夫的诸多文学业绩。三岛生于1925年,原名平冈公威,是东京一个富庶家庭的长子,三岛由纪夫则是笔名。他在校成绩优异,1944年以班级第一的佳绩毕业于贵族学生院,年仅十九岁便专程前往东京中部的皇宫领奖——奖品是一块银怀表——还是由裕仁天皇亲自授予的。(次年,也就是1945年,三岛接到征兵入伍通知,但没有通过体格检查,因此,一生都没有参加过日本军队。)战后,三岛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又通过了最艰难、最严格的职业面试,终于顺利地进入大藏省工作。但不久之后,正当他有望调任地方税务局局长时,却毅然辞去了官职,决定当专业作家——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职业选择。三岛就此抓住机遇,完成了令其成名的长篇处女作小说:《假面的告白》,触及同性恋的主题,于1949年正式出版。日本文坛盛赞这位二十四岁的文学“天才”。由此开始,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问世,速度惊人。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包括:《潮骚》(1954年),一部日本版的《达芙妮与克洛埃》;《金阁寺》(1956年),取材于发生于京都的一起著名纵火案——战后不久,因一名僧人纵火,京都最著名的古刹毁于一旦。这两部作品都被翻译成英文,并于1950年代在美国出版。(虽然是《假面的告白》的译稿最先完成,但搁置几年后才出版发行,如此一来,就让《潮骚》这本相对来说更传统的小说抢先面世,由此奠定三岛由纪夫在西方文坛的显赫地位,被评论界公认为一位不同凡响的新锐作家。) 罗德里克说,三岛不只是小说家。他还是剧作家、体育家和电影演员。他刚刚完成一部根据他的短篇小说《忧国》改编的电影,并担任主角:一位三十年代的日本年轻军官。故事描述了军官和妻子共同自杀的过程:军官剖腹、妻子割喉。罗德里克总结道,三岛是一个多面体,就好比莱奥纳多·达·芬奇再现于现代日本。这段有关达·芬奇的赞言略显夸张,得到的是三岛君慎重而含蓄的微笑。
接着,三岛站了起来。他的演说主要是在谈论自己的战时经历。他描绘了东京在1945年3月遭受的轰炸、熊熊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成千上百的东京市民在这个恐怖之夜丧生。“那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烟火表演。”他以一种诙谐的语气说道。当演说进入尾声,他用其语法虽然未必正确但铿锵有力的英语慷慨陈词。最后竟突然提到了他的太太,令演说戛然而止。(“瑶子没有想象力。”—说完,他微笑着扮了个鬼脸。)
在这平和的日子里,我们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有时候——仍然是这些逝去的记忆反复浮现于我的脑海(三岛在谈论他的婚后生活)。
那就是战时的记忆。我还记得一个场景,是在战时的,那时候我在飞机厂工作。
那天放了一场电影,为了让做工的学生们娱乐一下,影片是根据横光利一先生的小说改编的。时间可能是在1945年5月,是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和所有学生一样,无法相信我们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我记得电影里有这样一幕,画面里有一条街道,是银座的一条街,是战前的模样,霓虹纷艳闪烁,美丽极了;虽然屏幕上的霓虹在闪耀,但我们都坚信:此生无法看尽这样的景致,此生也再无可能见到这样的景致。可是,正如各位所知,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地看到了,就在银座的大街上,霓虹灯变得越来越多。可是有时候,当战时记忆重现于我的脑海,思维中便有些许困惑。在战时电影中的那些霓虹灯,以及在银座街道上的真切的霓虹灯——我无法分辨哪一个才是幻觉。
这可能就是我们……我最基本的主旨,也是我关于文学的最本质上的浪漫主义观念。都是死亡的回忆……还有关于幻觉的难题。
三岛说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力图清晰。他的英语发音很古怪,极有特质:把“artist(艺术家)”读成“urtist”。尽管他的英语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都有一点不规范,但这似乎根本不能困扰到他。他完全没有装腔作势——在这一点上,他实在不像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