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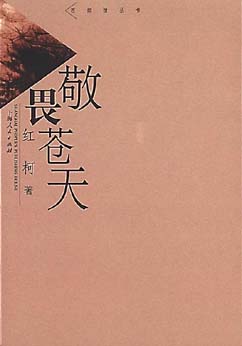 红柯的散文集《敬畏苍天》大致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敬畏苍天部分,主要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以及民族风情。其次是关于大西北的人和自然的故事。再次是文学的西部精神,是关于文学的随笔。红柯作品的最动人之处,是把大漠孤烟直的边地与特有的民族风情糅合在一起。骏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地域不同,形成了艺术创作风格的不一样。红柯是从泥土中滚出来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与他客居新疆十年的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带有新疆边地人民特有的气质,那地方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其魅力就在于他用绚烂多彩的文笔,用他特有的道德观和历史视角描绘出一幅幅色彩奇异的新疆地理、风俗、民族生活方式的画卷,使他迥异于同在新疆的作家周涛,形成了只有红柯才有的风格特色。民族的风俗民情比自然景观具有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蕴涵,它们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红柯把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结合起来,创造出意境深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抒情画卷。自然照耀古人也照耀今人,勾画出人生的背景,涂抹着人类的气质和性格的色调。然而地理环境并不承担文化责任,它只有在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取得联系时,才对人的性格、文化形态起到某种作用。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柯笔下更多的是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异域空间的历史人物,哪怕是那些颇受争议甚至为人们所唾弃的历史人物。当然,如果我们把红柯当作一个“民族抒情画卷的歌手是远远不够的,透过“民族画卷”的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纠缠不清的“生命情结”和“历史情结”。籍此高生命的伟力,呼唤血性精神,历史只是生命力的表象特征,红柯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的历史本身是人性退化的历史,人性高扬的阶段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终结,尼采、福柯的意义就在这里。” 红柯的散文集《敬畏苍天》大致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敬畏苍天部分,主要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以及民族风情。其次是关于大西北的人和自然的故事。再次是文学的西部精神,是关于文学的随笔。红柯作品的最动人之处,是把大漠孤烟直的边地与特有的民族风情糅合在一起。骏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地域不同,形成了艺术创作风格的不一样。红柯是从泥土中滚出来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与他客居新疆十年的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带有新疆边地人民特有的气质,那地方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其魅力就在于他用绚烂多彩的文笔,用他特有的道德观和历史视角描绘出一幅幅色彩奇异的新疆地理、风俗、民族生活方式的画卷,使他迥异于同在新疆的作家周涛,形成了只有红柯才有的风格特色。民族的风俗民情比自然景观具有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蕴涵,它们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红柯把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结合起来,创造出意境深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抒情画卷。自然照耀古人也照耀今人,勾画出人生的背景,涂抹着人类的气质和性格的色调。然而地理环境并不承担文化责任,它只有在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取得联系时,才对人的性格、文化形态起到某种作用。这就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柯笔下更多的是具有历史纵深感和异域空间的历史人物,哪怕是那些颇受争议甚至为人们所唾弃的历史人物。当然,如果我们把红柯当作一个“民族抒情画卷的歌手是远远不够的,透过“民族画卷”的背后,我们分明看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纠缠不清的“生命情结”和“历史情结”。籍此高生命的伟力,呼唤血性精神,历史只是生命力的表象特征,红柯在一次访谈中说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的历史本身是人性退化的历史,人性高扬的阶段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终结,尼采、福柯的意义就在这里。”
红柯的想象力是丰富而巨大的,只能在历史的天空和异域的草原里驰骋,读红柯的散文与小说,有时候很难分清这两种文体的区别,他写西部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篇关于西部文物风情特别是具有新疆浓郁民族地域特色的散记,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在于:散文更直接地接近作家的心灵、人格和生命本原,如果说他的小说是重在强悍生命形象的塑造,那么他的散文则是这些强悍生命的精神、人格、灵魂和情感的居所。红柯的散文更直接逼进了他的心灵深处,并带着他的血温、情绪和生命气息。他的散文无论是写历史题材,还是写亲情和友情,都具有小说般的叙述风格。而在语言方面,红柯都追求“陌生化”效果,努力打破生活语言的平面化,使人产生新鲜、奇崛的审美体验。
作为关中弟子,红柯具有深厚的中原儒家文化背景,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而中原文化,尤其是陕西,一个庄稼汉都充满帝王的韬略,每根头发都在算计中。”当这种背景和他客居新疆十年的生命体验相碰撞,而这种体验又往往与关中的生活文化底蕴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时,中原文化的温文尔雅、工于心计与西部的荒凉、亘远和马背民族特有的强悍与烈性就造成了强烈的审美冲突,无论何种地域文化,都是以生命的深刻体验为线索,以追寻历史为语言的外壳或者说历史是生命体验的载体。在他的散文创作里,始终贯穿着对强悍生命的热情讴歌,对生命最原始的状态所迸发的力量的崇敬,“血性”与潜在的“退化”是红柯对历史的追思的结果,从尔远距离透视人生和解剖历史,借历史任务来表达现代人生存的困惑与迷茫。弗洛依德说过,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牺牲和压抑人性为前提和代价的。在《天才之境》里,红柯以绚烂德语言穿透历史德层层迷雾,还原一个具有强悍生命德天才诗人形象,文章这样写道::“李白生于此,并且度过了他的童年。在儒家经典之前,他首先解读的是胡人的马群和宝剑,是中亚的群山草原戈壁,是沙之书风之书大地之书;”红柯借李白这一天才诗人,表达了对一种生命伟力和豪迈人生的敬仰。但我们也分明感受到红柯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是热情地讴歌那些带有异域色彩的历史人物和草原骑手,高扬生命力,呼唤血性精神,大自然的豪气和大气在大西北处处展现着。西北磅礴的天地孕育了大气磅礴的生灵,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生命也无不心胸宽广若大河滔滔,马和骑手便是大西北所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另一方面对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所体现出生命“血性”的退化和生命张力的减弱进行潜在的批评和担忧。我们几乎不难在红柯的散文中找到这样的句子:“居于沙漠的草原人其心灵与躯体是一致的,灵魂是虔敬的。而居于沃野的汉人却那么浮躁狂妄散乱,心灵荒凉而干旱”(《敬畏苍天》)。“《红楼梦》与《金瓶梅》一样,写的是一个民族在人种上的退步与衰亡。……日本兵一个大队可以抗拒中国一个军,台儿庄大战也是四十万中国军队与三万日本兵的血战,除过牺牲与爱国热情外,生命应有的剽悍与野性全没了。我们的剽悍与野性,全都体现为市井无赖对同胞的蹂躏;在民族整体的生命意识里,却没有一种精神。”(《一个剽悍民族的文学世界》)在这些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情感的句子里,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历史情结和想象表达出内心的矛盾,对生命力的天然亲和和对现代文明的潜在拒绝使红柯几乎所有的散文都深深烙上了“退化”的历史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