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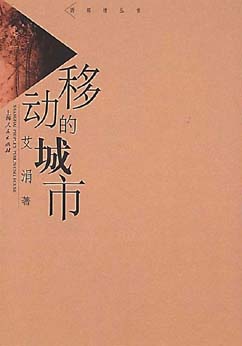 我和艾涓的认识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某个段落,那也是一个适宜于文学生长的季节。那时侯,艾涓的位置还在蒲白矿区的一个山洼里,年青而有热情,城府和沉重似还不容易在他身边立足,那时的艾涓像许多文学发烧友一样,正一头扑在诗歌的幻像里捕捉美丽的蜻蜓,连绵的平原大山和无际的天空正好适宜于孕育他的憧憬和抱负,后来艾涓的行囊里背着一份热情、一份纯真、一份想象、一份唐突,可能还有抑制不住的幸运感进入了西安。后来,艾涓的形象就明晰了起来,复杂了起来,他总是让我想起时下报刊上常常描绘的“北漂族”。如果说在西安有一些类似于“北漂族”的群落的话,那么艾涓的某个人生段落上可以写上重重的一笔。他是单纯率真的,可爱的鲁莽里更多地流露的是热情和无畏的可贵气质,可是这还不是拥抱这个城市的充足条件。文学梦的生长必然伴随着生存的烦恼。生活和文学构成了矛盾。这个矛盾过程又造成了他的许多性格矛盾,单纯里时而有莽撞,热情里间或有屈辱,潇脱的姿态、急切的认同欲望常常与无奈和激愤混杂一起。不断地失位,不断地复位。不能说他是边缘的,但他总是匆忙的,有时脸上流露出急躁和焦虑,那是他都意识不到的长期的身份认同的心迹的流露。在这个城市的移动中,时光也给这个漂泊者涂上了复杂的油彩。 我和艾涓的认识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某个段落,那也是一个适宜于文学生长的季节。那时侯,艾涓的位置还在蒲白矿区的一个山洼里,年青而有热情,城府和沉重似还不容易在他身边立足,那时的艾涓像许多文学发烧友一样,正一头扑在诗歌的幻像里捕捉美丽的蜻蜓,连绵的平原大山和无际的天空正好适宜于孕育他的憧憬和抱负,后来艾涓的行囊里背着一份热情、一份纯真、一份想象、一份唐突,可能还有抑制不住的幸运感进入了西安。后来,艾涓的形象就明晰了起来,复杂了起来,他总是让我想起时下报刊上常常描绘的“北漂族”。如果说在西安有一些类似于“北漂族”的群落的话,那么艾涓的某个人生段落上可以写上重重的一笔。他是单纯率真的,可爱的鲁莽里更多地流露的是热情和无畏的可贵气质,可是这还不是拥抱这个城市的充足条件。文学梦的生长必然伴随着生存的烦恼。生活和文学构成了矛盾。这个矛盾过程又造成了他的许多性格矛盾,单纯里时而有莽撞,热情里间或有屈辱,潇脱的姿态、急切的认同欲望常常与无奈和激愤混杂一起。不断地失位,不断地复位。不能说他是边缘的,但他总是匆忙的,有时脸上流露出急躁和焦虑,那是他都意识不到的长期的身份认同的心迹的流露。在这个城市的移动中,时光也给这个漂泊者涂上了复杂的油彩。
以我对艾涓的了解,这一切都可以在他的文字中读出来,甚至说不清是文章还是别的什么凸现了艾涓的面像。当然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可以读出来,那就是艾涓从来就没有放弃他心中很深的文学情结。许多都变了,一些东西遭到磨损甚或变形,但他那一份执著没有变。尽管作者说他常常无奈地干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写一些自己并非愿意写的东西,这也难以掩映他的本真。了解他的人会知道,这本随笔集《移动的城市》部分地就是他心迹的写照。有时候,职业和他的爱好他的写作形成了矛盾,但他总是在努力克服着这种矛盾,并且努力突破职业的束缚,在写作中显示出自己的个性来。当然,还不能否认这样的情况,这就是职业的要求提升着他的欲望,刺激着他的才情,给他带来了并不是意外的收获。艾涓的说法部分地带着自嘲,部分地带着真诚。恐怕此后的判断应该是这样的,财富和损失都有比例。况且就艾涓的写作呈现而言,他有妥协,但有时候写作和职业是一轨制的。艾涓有几篇关于陕西文坛、陕西书坛的纵横扫描,部分是命笔之作,部分是言说欲望的实现。这几篇扫描,现在读来,仍能读出热情,读出率真,他的笔下有对陕西文坛群体形象的勾勒,更有直面现象的勇气和识见。虽然有些判断和猜想失之平面,但仍能读出他区别于一般新闻人的文学素养,读出他介入文坛的深度,读出他的鲜明来。也许,一个站在半山腰里的观察者看到的现象就是本质,或就是本质的一个层面,神秘和简单有时是互为表里的,况且,艾涓还不仅仅是个观察者。
许多人都说过艾涓的见地、灵气和才情,这在《移动的城市》中的一些文章里有所见证。按照艾涓的说法推论,这大概是他克服了职业限制的产物。放下这个可以讨论的推论不说,艾涓的一些文章是干净和有质量的。他写周明,是对人们熟知的周明的个体视角的观察和勾勒,一下子唤起了熟知的人们的亲和力。“语言的朴实无华,感情的真挚醇厚,叙述的亲切平和与友善”是艾涓对周明散文风格的感知和概括,我相信大部分人是认同艾涓的赏鉴力和概括力的。艾涓对朋友炜评的描画,由表及里,由性格而及心灵,排除了散漫和随意,读得出投入和深挚的流露。“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初期时代,多数文化人的处境都是尴尬的,不为窗外的喧嚣所动,恬淡自守的确是一种可贵的品格”,这段对炜评性格的透示,是有深度的。当然里面有艾涓本人心迹的容入,甚或让人联想这个时代许多矛盾体的投影。艾涓的《诗人丁斯》也是追求形象和思想并重,在扑面而来的形象写真中凸现诗人的品性,诗歌的质地和品性,在形象展示之后,艾涓有这样的提升,“颓废与毁灭,是丁斯诗的主题;自嘲与自谑,是他诗的表现方式”,这是显示了领悟力和识见深度的表述。由于朋友的缘故,我和张炬有过交往,这次读到艾涓的《我观张炬山水画》,不仅仅是认同感涌上心头,艾涓对张炬山水画的评判,已是用一般的到位不能表述,他是由一般的鉴赏入手而又超越了一般的鉴赏判断,达到了审美层面和生命力层面的揭示。他指出,在张炬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作者的寂寞与孤独,甚至是一种浓浓的悲剧意识。类似于这样的文章,我想艾涓是自知它的孕育过程的,艾涓大概也知道,他是如何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