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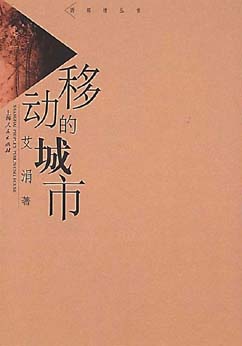 和刘辉(笔名艾涓)最初的相识,是1989年在西北大学。也是秋季,来自全国各地一些或年长或年少的文人们聚拢在西安这座古老而又新兴的城市边缘,成为这所大学最后一届作家班的学员。既然是文人聚堆,相轻之风自然难免,甚至开学几个月了不少人还佯装叫不出同学的名字。那时的刘辉很“土”,一套早已不合时宜的旧军装终日不除,斜背一个军用挎包,胸前别着一个闪亮的毛主席像章,用西安人的流行语叫“特的很”,可刘辉对人热情,也不伪善。 和刘辉(笔名艾涓)最初的相识,是1989年在西北大学。也是秋季,来自全国各地一些或年长或年少的文人们聚拢在西安这座古老而又新兴的城市边缘,成为这所大学最后一届作家班的学员。既然是文人聚堆,相轻之风自然难免,甚至开学几个月了不少人还佯装叫不出同学的名字。那时的刘辉很“土”,一套早已不合时宜的旧军装终日不除,斜背一个军用挎包,胸前别着一个闪亮的毛主席像章,用西安人的流行语叫“特的很”,可刘辉对人热情,也不伪善。
转眼到了寒假,我因忙而误了最后一趟去火车站的10路公交车,心里便急,有时冬夜。这时刘辉出现在校门口,他不但准确地叫了我的名字,而且变戏法般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硬是驮着我送了一程。从此,我便对这个笔名叫艾涓的家伙有了无限好感。毕业时正感上“孔雀东南飞”年代,生长在西安的同学大都经受不住沿海经济的诱惑,纷纷去了广东、海南等地,而我与刘辉却臭味相投地因为爱情和迷恋西安古老的文化,甘心做了这座城市屋檐下的异乡游子。
这些年,我先后在《劳动周报》和《消费者导报》经营着副刊,刘辉也精力充沛地在诸多报刊干过采编和担任过领导职务。相同的经历让我们产生了相同的语言,类似的磨难让我们拥有了类似的认识。虽然同是西安城里的外地人,但刘辉在这座城市里呼吸比我更顺畅,仿佛是一条游动的“雄鱼”,欢快而勇猛。尤其这些年他“多管齐下”,既在报刊界疯狂地制造文字影响着不同层次的读者,又在书画圈里“指手画脚”、“舞笔弄墨”,使得自己的书法作品也偶露峥嵘,让我羡慕不已。
一年一度秋又至。刘辉在忙于工作的同时,令人吃惊地推出新作,与陕西的文坛大腕陈忠实、高建群、红柯、方英文等组成一个叫“西部情”的方阵闹腾文坛。刘辉这条“雄鱼”的精力果然旺盛。
这册《移动的城市》随笔集所选作品大都写在一个文化衰弱的时代,刘辉顽强地在求生计之余“爬格子”的精神令人敬佩。“休闲的贾平凹”、“走虫爬出高老庄”真实生动地描述了文坛鬼才的独特个性;“陈忠实的日子”、“莫言西安吐真情”、“与张艺谋有关的”等让读者从多视角对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创作有所了解;在物欲横流,人们更多地关注金钱的今天,刘辉以轻松幽默之笔展现书画界文人的心路历程,为读者补充精神食粮;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坛的“陕西东征”现象,以及陕西书坛出现的冷落困惑和茫然进行剖析。刘辉有着独特的见解,令人叹服。
当然,这个集子却不是刘辉生活的全部。10多年来,除了吃喝拉撒,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干一些身不由己的事,写一些并非自己愿意写的文章,这是生活所迫。我知道,为了在这座移动的城市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坐标,他有时很难静下心来读一些自己愿意读的书,写自己愿意写的文章,偶有闲暇,也被无穷无尽的应酬占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真诚地向人们展示了他的文学情结。就像撒满种子的土地,刘辉的外表是朴素的,而其内心却蕴藏着破土的力量,在移动的城市里,他能如故地歌颂真诚并再一次出版文集,这结果是必然的。
刘辉为人的品德决定了文风的正直和纯朴。他的文章既不故作高深、追求怪异,也不无病呻吟,他文中的物象的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具特色的,有很多的美学价值。读刘辉的文章,你分明能感受到一种爱--对生活的爱,对责任的爱。这也是有良知的文化人独特的爱。而且,他把这种爱升华成精神宗教。
此刻,窗外正飘着黄鸟一样的叶片,黄昏的斜阳灿烂地照着这座古城。我相信,在这深秋的黄昏,刘辉就如同忧郁的古典诗人,依然独守在能安妥自己灵魂的--城市里那一块安然孤寂的净土上,但我不知道刘辉此刻是否如我一样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终年忙碌而又贫穷的亲人?在移动的城市这篇多情而复杂的热土上,我坚信刘辉孤独的身影还会无悔地闪现,祈愿在下一个集子中,我们能听到刘辉关于故乡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