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文化是内涵极其丰富的宝藏,对于江南文化的研究可以从多领域、多角度、多方法入手。本次推送选摘自《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书中探讨了明清之际江南的社会文化图景,例举江南宏观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面向,观照江南文化的多样化特质,从而勾勒出江南整体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变迁。
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曾经形成的江南现象的中心感,以及中国区域史研究中的江南核心性[1],是构建全国性历史叙述的重要内容。倘从地缘关系要素的角度着眼,江南的地缘结构,既有时代共性,又是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尤其是从明代中后期以来,因不同政治层面的影响,江南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如何更好地理解与认识江南历史地位的形成与江南区域研究的核心意义,表面上多在于经济地位的论述分析,实际上仍在政治性的把握。
明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影响着社会与国家的“逋赋”,深刻地体现出王朝统治的制度性与结构性的大问题[3];明末江南城镇广泛兴起的“市民运动”,已表现出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内部分裂”的样貌,在一定程度内已含有一种“启蒙运动”的意义。[4]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力的无锡东林学风(特别是务实与经世),与苏南望族文化的成长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相得益彰[5];东林、复社及其代表性成员的言行,形成了江南士人独特的精神面貌,都无法与当时的政治相剥离,超然于政治之外。这与清初以来“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的状态并不相侔,也从反面表明政治在其间的巨大影响力。[6]再如明末政治动乱与战争危机情势下的江南士人风尚,在保存经世之心外,多崇尚谈兵论剑的活动,终使习武风尚发展成为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7]
至于地方上长期存在的乡里组织[8]、安全系统(譬如治安方面有里甲、保甲与火甲[9]、巡检制度,地方武装方面的乡兵、民壮等,生活空间方面的城防与水栅等[10],社会保障方面有覆盖城乡地区的民间强大的慈善组织与善举活动等[11]),为王朝统治在江南的稳固,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士人的精神生活和信仰领域,虽然与经济活动一样,会有超越政治控制框架的表现,而且官方儒学经典、祭典和民间地方祭祀系统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但在帝制时代,最终还是要受到政治的约束,国家权力是影响民间社会最大的变量。[12]江南地方社会生活中,牵动地域社会整体注意力的水利事业,更关系着江南社会与生活的共同利益,虽然其间地方力量是官府的重要依靠,但国家的调配与控制仍然具有关键意义,甚至是更为积极的角色。[13]
邹逸麟在江南研究三十年回顾中,强调除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要。他概括性地指出,从春秋战国以来,“江南”地区不仅存在欲争霸中原的政治势力,而且到南北对峙时期,江南成了中原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地区,到高度集权的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中央王朝时存戒备又不得不依靠的地区。[14]这些在江南政治史研究中都已构成重要的内容,而且还可表达出如何在区域史研究中体现国家历史,以及国家如何反映于地方史脉络中的问题与思考[15],特别是在晚近以来江南政治历史的复杂进程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尤宜值得重视。[16]
总之,传统时代江南地区存在的强大的士大夫群体,可以抗衡国家,也可以深入民间社会[17],有“士民公议”或“地方公议”的政治习惯及其实践[18],但其背后一直是帝制国家与王权在左右。[19]士人经由个人的努力,参加科举,取得官位,进入政界,但要保持其政治地位,除了依赖国家,最有效的办法,还有固结乡里关系而扩大其影响。这种乡里关系形成的集团,往往能冲破地域性的限制。到了清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虽依旧存在,可是他们的政治活动却受到更多的限制。[20]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在国家与地方权力格局发生重要转变的情势下,地方社会中占据最关键角色的士绅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21],更是契合江南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江南社会的形态,自然也不会超脱帝制农商社会的基本框架。[22]在国家政治与地方治理这样的理论关怀下,不少研究已作了新的探讨或扩展[23],对江南史研究而言是一种新的气象与格局,是值得注意与勠力进取的方向。
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从而更明显地呈现江南地区孕育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区域以及全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链接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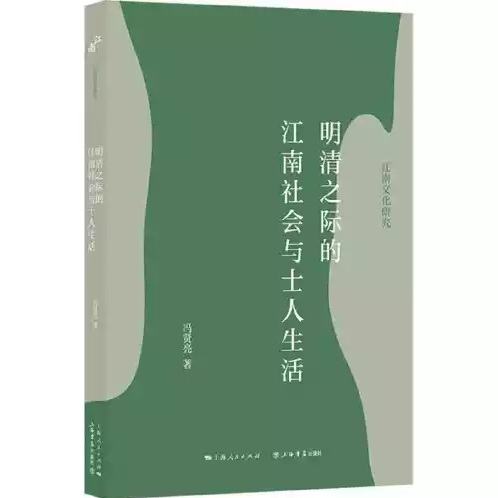
“江南文化研究”
《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
冯贤亮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