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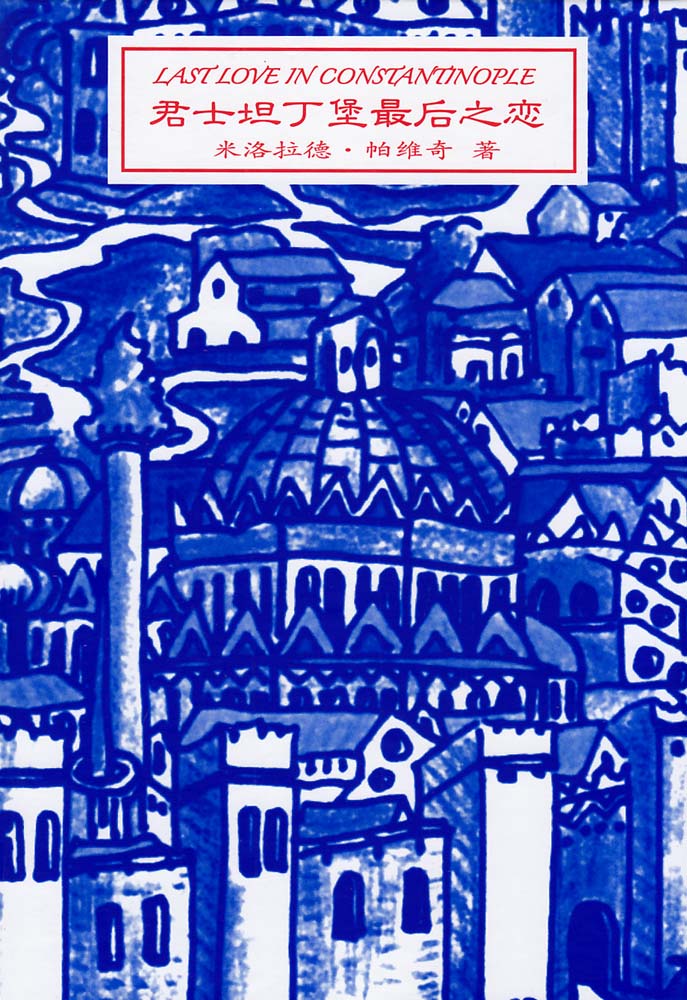 继《哈扎尔辞典》之后,塞尔维亚著名的天才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又一部奇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译本。 继《哈扎尔辞典》之后,塞尔维亚著名的天才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又一部奇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中译本。
这部书的最奇之处是让读者决定从何处开始阅读,又从何处结束阅读。整部书以塔罗牌的形式构成,三组牌,各七张,每一张牌对应一定的人物和一段相对完整的故事,每个根据塔罗牌上的形象(魔法师、女皇、恋人、战车……)为线索组织起来的章节均具有天然的魅惑、神秘的寓意。
无论是按一般的小说阅读顺序,还是根据作者给出的几个塔罗牌牌阵要求的次序去阅读对应的篇章,或者干脆打乱章节的编号去读,《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都会通过读者的阅读来完成一次“创造”。
帕维奇经常建议译者
照原文样子去直译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译者是知名出版人、文学翻译家曹元勇。他与帕维奇的作品结缘,是在20年前的初夏。
当时,他乘火车南下广州去联系工作,躺在上铺毫无睡意地读着当时《花城》杂志转载的一部外国小说——《哈扎尔辞典》;夜愈深,他愈是在那部小说里陷得深远。结果则是,那一夜的车程没有让他和广州结缘,反倒是让陌生的帕维奇和神奇的《哈扎尔辞典》在他心目中的文学圣殿里占据了显著的位置。
2012年初,曹元勇第一次去美国,第一次走进纽约的思川书店(StrandBookstore)。他原想淘一本趁手的袖珍版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集,孰料却与三本英文版的帕维奇作品不期而遇。那三本书——《哈扎尔辞典》、《风的内侧,或关于希洛和勒安得耳的小说》和《茶水绘制的风景画》,就像某人寄放在那儿的礼物,等着他千里迢迢赶来领走。当年岁末,在美国生活的两个朋友得知曹元勇钟爱帕维奇的书,又特意寄来英文版的《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贝尔格莱德简史》。也就是在那时,曹元勇产生了翻译帕维奇的作品、并借此向他致敬的念头。这才有了今天的《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译本。
曹元勇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篇幅不长,不足10万字,但他译得小心翼翼。在翻译过程中,帕维奇先生的遗孀——作家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维奇(JasminaMihajlovi)女士给了他很多帮助。通过Email,雅斯米娜女士不仅将书中一些罕见的知识点、难解的隐喻表达和塞尔维亚民间表述,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并且让他了解到基督教文化里有一种观念:上帝与名词联系在一起,魔鬼与动词联系在一起。
另外,她告诉曹元勇:“帕维奇本人经常建议他的译者照原文的样子去直译,只要你这样做,你的译文就会是理想的,因为语言中特别的东西——那些让读者惊讶、让读者反复琢磨的词句——都会得到保留。”尤其是针对帕维奇作品里常出现的非常规词句,比如《君士坦丁堡之恋》“太阳”一章中的“twobowlsofwarmGod’stears,abreadedgaze(两碗热腾腾的上帝之泪,一份裹着面包屑的凝视)”,雅斯米娜女士认为只要照字面意思翻译就好。
了解帕维奇
首先要了解南斯拉夫
无论是《哈扎尔辞典》,还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两书都可被称为“奇书”。《哈扎尔辞典》1994年在国内就有了中文节译本,之后分为阴本和阳本的完整版又分别在1998年、2013年、2015年多次出版;这部奇书引起的波澜至今犹在。
了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历史,是深入帕维奇文学世界和思想的前提。在《哈扎尔辞典》出版时,帕维奇的祖国还是拥有6个加盟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而到了写《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他曾经的祖国却已分崩离析;到他2009年去世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塞尔维亚人。
学者郭建龙曾分析,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南斯拉夫的位置决定了它始终在东西方之间,是各个势力插足、并吞和拉拢的对象,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由于传统不一,其选择也充满了摇摆和不确定性。在铁托时期,这个铁腕统治者试图通过共产主义信仰来把三大宗教势力都凝聚起来,但是,当1980年铁托去世之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逐渐走向了解体。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给了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的机会,这场巨大的崩盘直到2006年黑山独立才结束,除了加盟共和国各自独立之外,2008年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也宣布独立,并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等部分国家的承认。
帕维奇的一生(1929~2009),恰好经历了南斯拉夫从王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再到解体的整个过程。他不仅是南斯拉夫人,还来自南斯拉夫国家最主体的塞尔维亚,对于南斯拉夫的不稳定以及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摇摆都深有体会。而他的作品虽然在结构和可能性上充满了实验性,其主题却仍然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世界、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的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