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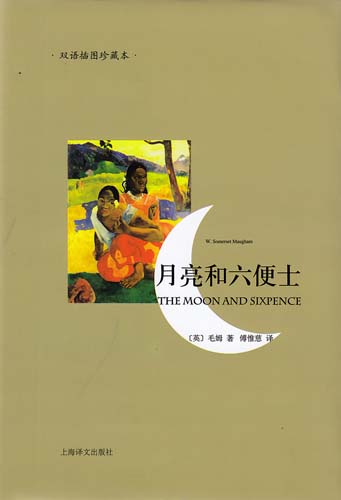 3月16日下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发微博称:“接同事电话,惊悉傅惟慈先生今早因突发哮喘去世。一代有风骨,有格调,有性情的前辈,又弱一个。先生旷达死生,闻知要将遗体捐献做医学研究,身后不搞仪式。”这则消息引来很多文学界人士和网友的悼念。记者采访确认了这一消息,著名翻译家傅惟慈于3月16日上午十点在积水潭医院逝世,享年91岁。昨日中午13时,积水潭医院太平间举行了小型的遗体告别仪式。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参加遗体告别的上海读客图书的编辑杨芳州,听她讲述与傅老的一面之缘。 3月16日下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发微博称:“接同事电话,惊悉傅惟慈先生今早因突发哮喘去世。一代有风骨,有格调,有性情的前辈,又弱一个。先生旷达死生,闻知要将遗体捐献做医学研究,身后不搞仪式。”这则消息引来很多文学界人士和网友的悼念。记者采访确认了这一消息,著名翻译家傅惟慈于3月16日上午十点在积水潭医院逝世,享年91岁。昨日中午13时,积水潭医院太平间举行了小型的遗体告别仪式。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参加遗体告别的上海读客图书的编辑杨芳州,听她讲述与傅老的一面之缘。
格林、毛姆重要译者
傅惟慈曾用名傅韦,1923年生于哈尔滨。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和文学,195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文革”后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主要译作有《狱中书简》、《席勒评传》、托玛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等作品,还曾与董乐山合译《动物农场》、《1984》等书,影响巨大。2008年,傅惟慈的个人作品集《牌戏人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记者了解到,傅惟慈一直有肺气肿、肾功能不全等问题,去年下半年曾经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傅惟慈的女儿透露,最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总是会喘,一天不如一天,在家要坐轮椅,“但是脑子依然不坏,身体可以的时候,对什么都有兴趣。”前日早上上完厕所,他气喘发作,气捯不上来,送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
昨日参加了遗体告别的杨芳州告诉记者:“下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傅惟慈老师的告别仪式。傅老先生在2007年就与老伴一起做好了遗体捐献的认证,中午的仪式,也是与协和医科大学的交接仪式。现场只有30位左右的亲友到场,傅老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在,其他孙辈及亲属因在国外都还未来得及赶回。”她十分遗憾地说:“年前打电话给傅老曾说‘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再去看您。’傅老说:‘好好。我对你挺有好感的,你一定要来。另外,我这里小院子还可以办party,吃烧烤,不少人都来吃过。下次我邀请你,你可以带上你爱人和朋友,想带多少都可以。’没想到,这就是我和傅老先生的最后一次通话。”
玩心重、爱喝酒
傅惟慈去世的消息一出,文艺界人士史航、杨葵、任晓雯等纷纷在微博上悼念这位翻译家,还有不少网友回忆起当年读傅惟慈的译作时的感受。
韩敬群用一首“四根古柏卧王城,译笔中藏百万兵。几见蚍蜉摇大树,早将牌戏寄浮生。满园花发余香久,一曲声高酒盏倾。耆旧襄阳零落尽,去来无迹若为情”来纪念傅老的翻译生涯。他说:“很多人都读过他的《月亮和六便士》,算是一代人的记忆。我觉得像傅惟慈、董乐山那代翻译家,不仅仅是把翻译当成一种养家糊口的工具,而是有自己的情怀在里面。”
作家、出版人杨葵则回忆起几年前在《过得去》一书中记录的与傅老交往的点滴:“他住在新街口一个胡同里的胡同,独门独院。听说那条胡同原本都是他家祖产。老先生特别可爱,玩心重,喜欢古典音乐,喜欢喝酒,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常在家组织小型party,拌点凉菜,烤点面包,买点熟肉,大酒一喝至深夜,西式文艺沙龙气息浓厚。”他还表示,傅老酷爱旅游,“只要在家呆超过半年,就浑身痒,经常背个小军挎就出门了。他给我看他的护照,说记不清这是第几本。护照里,欧美多国使馆的签证花花绿绿,只剩一两张空白页,又该换新的了。”而傅惟慈生前也曾表示:“我喜欢到处玩,到处跑。我的人生观就是,一切都是作为游戏,要寻找些乐趣。”
作家任晓雯也在微博上表示:“作为一名中文写作者,我非常感激有那么多优秀的译者,能让我读到各种语言的好作品。没有他们,当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会完全不同。翻译是辛苦、寂寞、清贫的事业。向译者们致敬。向傅惟慈先生致敬。”
自称只是个“翻译匠”
记者昨日从上海读客图书了解到,读客将于2015年出版傅惟慈的旧译格雷厄姆·格林的《密使》、《一支出卖的枪》和《问题的核心》修订本。杨芳州告诉记者,“格林作品在国内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有译稿发行,最近的版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分别再出,这次签下的是上译文和译林‘吐出’的版权,算是捡了一个漏。”等到合约签好了拿到手里,杨芳州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傅惟慈先生,购买他的原译,并希望他来做格林系列的顾问。“电话联系的时候,老先生声如洪钟、思维敏捷、语速极快、表达清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先生爽快地答应了译稿的稿酬事宜,并约好登门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