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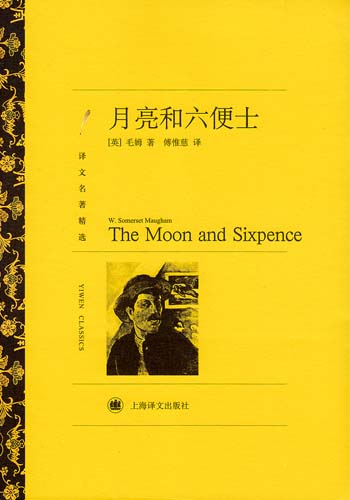 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是当代的文学经典,毛姆的文字也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范本。毛姆的创作始于19世纪末,一生写有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有评论家说毛姆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好,但我更喜欢他的长篇;有人说《刀锋》是毛姆的长篇代表作,并把其中的主人公拉里当作人生的偶像,但我更喜欢《月亮和六便士》,喜欢他笔下的阳光灿烂的塔希提岛—— 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是当代的文学经典,毛姆的文字也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范本。毛姆的创作始于19世纪末,一生写有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有评论家说毛姆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好,但我更喜欢他的长篇;有人说《刀锋》是毛姆的长篇代表作,并把其中的主人公拉里当作人生的偶像,但我更喜欢《月亮和六便士》,喜欢他笔下的阳光灿烂的塔希提岛——
太平洋烟波渺茫,浩瀚无垠,水上是一片碧空,群星熠熠……这就是塔希提;在热带雨林中,到处是椰子、甘蔗、香草,还有火山……这就是塔希提;
一片片郁郁苍苍的树木,有观赏不尽的色彩,有芬芳馥郁的气息,有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人世乐园就是塔希提。
看过毛姆的书知道了塔希提,看了高更的画更忘不了塔希提。
毛姆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活为原型写成了《月亮和六便士》,书和画相得益彰,作家以他非凡的才能创造美,画家以他非凡的才能为这个世界增添光彩。每读一次、每看一次,都会发现其中有新的信念和人生的意义。
书中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伦敦证券交易所里的职员,他有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有和蔼可亲、殷勤好客的妻子,有漂亮、健康的孩子,有房产,有稳定的收入……
还是用毛姆的话来说吧:“这一定是世间无数对夫妻的故事。这种生活模式给人以安详亲切之感。它使人想到一条平静的小河,蜿蜒流过绿茸茸的牧场,与郁郁的树荫交相掩映,直到泄入烟波浩渺的大海中。但是大海却总是那么平静,总是沉默无言、声色不动,你会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怪想法,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是“一种莫名的不安”和“一种强烈的愿望”,是“无法预见的刺激”使一切都改变了,某一天,故事的男主人公抛弃了原有的一切,他先是只身到巴黎画画,然后去了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可以忍饥挨饿,可以穷愁潦倒,可以被世人看作无情无义,但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家园,从此义无反顾,不再怀念巴黎或伦敦街头的灯火,不再留恋往日的生活。
毛姆写得太好了,傅惟慈先生的译文同样好。我手边的是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傅译本。再抄一段精彩的译文:“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的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可用苏东坡名句概括:“此心安处是吾乡。”
他在那里还为世界创造了美,在他笔下大地闪耀着那样明朗和浓艳的色彩。
在世上碌碌地生活,我们常常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就是找到了,也未必有能力和勇气投身其中。只能向往,向往塔希提。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这就是成功吗?我想,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毛姆的话不仅仅是说的他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