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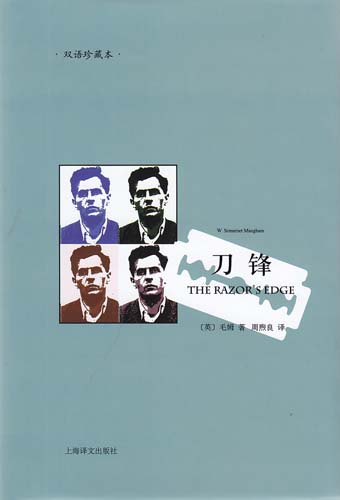 1月25日,也就是明天,为毛姆14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作品不朽的英国作家。 1月25日,也就是明天,为毛姆140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作品不朽的英国作家。
不知别人如何,我在难以自处时,常靠读小说来消胸中块垒。我的超级化食汤,是英国作家毛姆的《刀锋》。数次温读《刀锋》,起因不尽相同,却每奏和胃化淤之效,是以奉为良药。
主角退伍士兵拉里的人生在不停游荡和寻觅意义中进行,这游历中伴随着大量阅读,这是《刀锋》让浮游异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寻觅状态的我倍感亲近的主因。最早读的是周煦良先生译本,以后读了英文版,仍心折于周译简白古雅、大拙若巧的韵致。只见开初略嫌丰腴的伊莉莎白嗔怪拉里一声:“你这个狗蛋”,一股可爱的甜俗热乎乎扑面,怎能不惊艳译家的大胆?!还有拉里的感慨“死者死去的样子多么死啊”,死字用得神完气足,不由人不牢记。
《刀锋》中各角均为处世态度:拉里求道、伊莉莎白恋物、艾略特好名、格雷务实,初读时只以为利害分明,互为映衬,但隔些年温习仿佛中国山水移步换景,领悟不同。我内心本来只住了一个拉里,过几年有了伊莉莎白的位置;再过些时,艾略特叔父也搬了家当进来,犹如他爱重的奇彭代尔家具终于在我胸中妥置成套。这是《刀锋》奇妙之处——它的故事和人物耐读,而且常读常新,非经时间打磨不能深谙个中三昧。说变得世故也好,说成熟也罢,总之我在二十郎当头视拉里为理想人生的楷模时,完全忽略了他“晃膀子”和3000块遗产年奉的经济基础很有关系。这笔年金给了他一定程度的自由,避免在漫漫求索途中被生存之需逼到绝境。
起初,正直青年轻视伊莉莎白的物质至上和势利眼叔父艾略特以经营社会关系为要务——可不是理当如此?!若干年后,伊莉莎白的选择好理解了;一个处处帮你打点、又乐于助人的大方叔父也并非不能接受。又若干年,看后生们可劲儿找干爹,不免同意在结构性势利的社会里,现成一个头脑、资本、艺术品位俱全的叔父才是天赐靠山。他固然势利,却不害人,而且心地良善,待人宽厚,精于品鉴,无私帮助亲友。你的Linkedin社交网络中这样一个叔父作为第一联系人,是打通其他无数关卡的钥匙,无视其存在岂非浪费资源?
艾略特站在侄女的立场,要求未来的侄女婿要有家庭责任感,奋发有为,起码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与今日各家大人的要求毫无二致,何错之有?拉里成了艾叔父眼中的毒药,要怪社会的结构就是一个势结合利的大环,脱了扣,足以连累一整条生存链。
拉里非势利之徒,却十分明白,自己能率意而为,也仰仗3000块年金支撑;他天性优美,无意委就常规,他的范儿是世家公子诗意栖居“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过他不是空想者,服的是求知问道之役;读书行路与劳作成就他的隐于市。他也随遇而安,所以既能依从农妇的肉欲,也不拒绝落难女的求欢。
拉里幸运的求索有经济基础,这使他不至于殉道,也成为有效仿可能的榜样。我想起前几天所读野夫的《看不见的江湖》中人物——某个近乎失明的民间学人,在极端艰困中向坚壁猛力斩开生路,卷了刀刃。其生过于惨烈,意义风雨飘摇,苦难全面击退了优美,只余英勇和悲痛。比较境遇,以野夫的眼光来看,游历饱足之后散尽家财隐身江湖的拉里最多是一个“逸民”而已,不至于如毛姆那般捧高到“人中麟凤”吧?
1944年出版的《刀锋》铺写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和欧洲;当今之世,其风尚过时,人性与处世之道却没什么不同。艾略特、伊莉莎白和格雷等基本是主流,拉里基本是少数。当回首人生,唯我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满足点是不一样的,彼此难以做出评判。这正像一些势利鬼乍学得英文字“loser”(失败者)便如获至宝,动辄大喝一声“loser”以之斩定人生成败,未免近视。古诗谓“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我们多数人终其一生,能在得失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就已经很了不起。
青年人向往波澜壮阔的非凡,经风历雨后开始在意“中年饭软与茶清”,那其中有“不得已”;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世间刀锋无数,得救之道因人而异,各依条件尽力而为或能各安其所。因了人性的枷锁,一流志向的结局大可能是三流人生。而我们嘴里所谓一流三流,其实可能经不起推敲。
世人公认毛姆是二十世纪成功的英国作家和剧作家,但他自谦二流(所谓B list之列),这无妨其作品得到长久的知音。毛姆的小说建立了一个人性和处世的档案,目的不在于评论是非,却能丰富读者对世相的理解,宽阔胸怀,这就大有裨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