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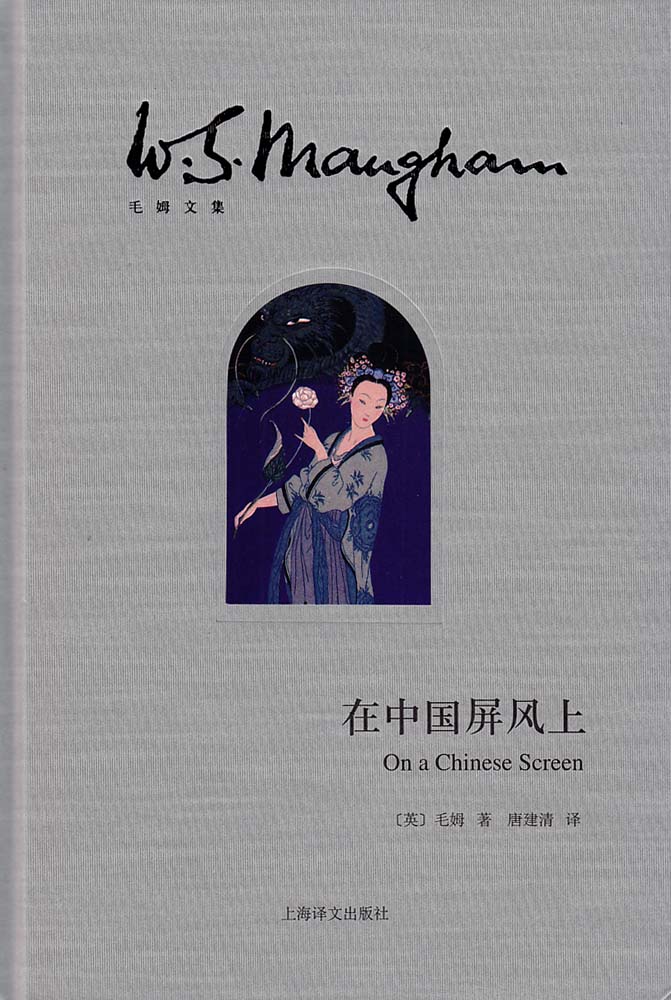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冬季,时年四十五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一千五百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即是他此次行程的产物,五十八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冬季,时年四十五岁的毛姆来到中国,溯长江而上一千五百英里,《在中国屏风上》即是他此次行程的产物,五十八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写成小说的“素材”,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
毛姆没有将这些随意的记录加工成小说,但正因为这样的随意,才让我们得以最大程度地体验到了在毛姆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时的纷繁感受。一如芥川龙之介所说,最难的艺术就是随随便便地送走人生。
毛姆的作品常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阅读感受——初读觉得波澜不惊,甚至平淡,但越读却越感到其中的蕴藉纷杂而层次丰富。
作为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毛姆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而尤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则当推他的长篇小说,譬如《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但毛姆其实更精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写有一百五十多个短篇,甚至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和“英国的莫泊桑”。但与如此赞誉相随的,是西方评论界对毛姆的另一种评价——认为身处20世纪的毛姆,在行文风格上没有什么现代主义的印记,在文学观念上已经落伍,甚至给他贴上了“二流作家”的标签。对于这样的评价,毛姆本人倒是很坦然。据称,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处于二流作家中最优秀的作家之列”。这样的自我定位颇有些自嘲的意味,但在其背后似又隐隐透出他对于自己文风的坚持。确实,毛姆向来追求平易和朴实的文风,这样的风格不仅在他的小说,在其他的作品——比如散文和随笔中更可见一斑。而这本《在中国屏风上》作为他为数不多的游记,在这点上则更显得耐人寻味。
毛姆在这本游记的序言中写道:
“我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我并没有一部日记,因为自十岁以后我就不记日记了,但每当遇见能激起我兴致的人或地方,我都会一一记录下来。我约莫觉得它们或许能成为创作一部小说的素材。随着素材的越积越多,我冒出一个想法,打算将它们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但当我把它们排列好,我从中发现了一种新鲜感,那些文字是在我记忆鲜活的时候记下来的,而如果我将它们精心加工成一个故事,这种感觉就会不复存在。我觉得我只需要将因匆忙造成的随意和马虎之处删去,使文稿变得更简洁些就够了。 ”
于是,我们得见了这本在随意中写就的“中国之行叙事”。正如毛姆所愿,他这样的处理方式,保有了这些轶事的新鲜感,或者说,最大程度地保有了毛姆当日所见所感的原生态。这五十八篇短文,犹如五十八个场景的连缀,让人仿佛跟随毛姆一起经历着这趟琐碎但真实的游历。从北京的城门到城里客店的布置,从看中国官员画画到晚间在稻田间的冥想,从路遇“苦力”到与汉学家的交流……这一路走来,我们通过毛姆的视角重新审视许多我们已经习焉不察的事物。
当然,毛姆惯常所擅长的对于人物的感知力和描写力是这本游记中极大的亮点。不管是蒙古人的首领、中国官员、路人还是他的英国同胞、传教士,这一路上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毛姆似乎总是以一种冷静而犀利的态度默默观察着,继而以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个极富特征的鲜明形象。甚至,他总是以一种很有距离感的第三人称“他/她”来作为主语描绘人物,而并不言明“他/她”是谁。于是,我们就如同在看他画一幅人物速写,随同他的描绘渐渐辨识这个人物的身份、性情乃至相貌。在这样的辨识过程中,我们的视界仿佛跟毛姆有了交集,于是,毛姆所意欲表达的种种便让人感同身受。
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名为《哲学家》的一篇。毛姆从如何获得与这位中国著名哲学家会面的机会入手,一路淡淡地描绘着自己眼中这位“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清瘦、“一双长得好看的、小小的手,干瘪得有些像爪子”又吸食鸦片的著名大儒。他们交谈,谈西方哲学,也谈中国文化,当然会有争辩或是碰撞,直到这位大儒最后给毛姆写了一幅书法。一切的叙述都是不露声色的平静,但不得不说,饶有意趣。这场会面就如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真实亲切。而当我在注释里得知这位大儒原来是辜鸿铭时,不仅大吃一惊!这位学者的形象从未如此贴近生活。或许正是因为毛姆并不刻意在叙述技巧或是行文特点上追求什么标新立异的“现代特点”,却反而能在在这样传统而从容平淡的叙述中真实地呈现出他所认识和感知到的人心世情。当然,他那些犀利而又精辟的观点,诸如“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哲学家的信念并非依据确实的证据,而是他自己的性情”等,蕴藉在这些看起来平淡的叙述中,便更显得出彩而耐人寻味。
在这本小书中的《漂泊者》一篇中,毛姆写道:“在写作中,更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这些小文朴实却精到犀利的风格,正体现了毛姆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