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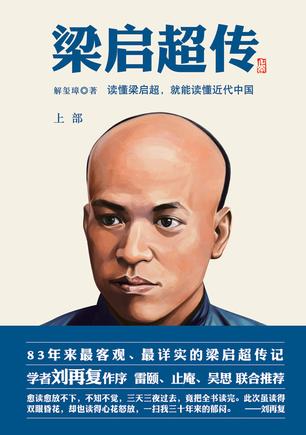 传统名家 现实发声 传统名家 现实发声
在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业界常有对今年一个“文学大年”的期许。对于2013年的严肃文学领域,也许需要注意的不仅是所谓“大年”名家们集中推出新作数量上的“爆发”。虽然就今年的传统文学出版状况来说,确有此类表现。另需注意的,还有存在于这批“50后”、“60后”名家群体笔下题材及立意的微妙变化。
如马原的《纠缠》,写遗产纠纷,当代这个高度利益化的时代,成为他写作的源泉。苏童的《黄雀记》,故事虽从上世纪70年代在南京流传广泛的一种舞蹈小拉开始,但也被《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价为一种历史跟当下的紧密结合。余华的《第七天》,在保留其荒诞和黑色幽默特色的基础上,也被称为离现实很近,如出现在作品中的“墓地贵”。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干脆把笔触落在“蚁族”身上。贾平凹的《带灯》,以一位基层维稳人员为主角,通过她带出当代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批掌握着主流文坛“话语权”的作家,作品似乎出现了从“个人化”向“公共化”的转变。当然,此类标签未必完全准确,因其以往的写作虽带有极强个人生活和创作风格的烙印,但总归是写人性、人生,进一步说,也不能说其脱离现实,但新近的作品确实能看出更多直面当下生活的意味。
对此的评价有了更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某作品创作有着纯文学与畅销书搭桥的意图,甚至某作品在创作水准上比以往作品似有下降,带着升级版社会新闻的浮躁。从这点上不难看出,以往这批作家对“当下”犹疑的原因: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已与老百姓自嘲的“屌丝”生活大为不同,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距离”在创作中的作用,正如苏童曾说的,刚倒出来的水难免有些浑浊,任何对于一个时代最精准的描述都是沉淀之后做出的。
然而,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传统名家为何在面对现实书写难度之时,还是纷纷或多或少更直白地面对了现实。是当下文学在困境中的变化,还是时代局中人的自然而为?又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这样想,不仅当下之新闻意味着未来之历史,当下之文学也为未来之历史提供着一面参照的镜子。
古典情怀 重入视野
在喧嚣日上的当下,文字的光芒及意义是否正在消散,一直是近年业内在探讨的话题。今年,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对“小而美”等文学形式的探讨,对以“平淡”姿态写作作家们的关注,正在令文学的古典情怀回归。这种情怀,在保持一种相对“遗世独立”的写作态度的同时,依旧指向现实、责任、关怀等文字的传统、纯粹价值。
在门罗获奖后的第一时间,众多业界人士都对当时这位只有一本单行本《逃离》在国内引进出版、80多岁的女作家表达了对其获奖实至名归的敬意以及毫不掩饰对其作品的喜爱之情。著名出版人韩敬群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门罗获奖,确实是一个‘纯文学意义上的奖励’。若因这位作家的获奖能使读者亲近高品质的文学,可谓幸事。她像一位文学的手作艺术者,寂静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学。”出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的门罗,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逐渐形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的写作风格。然而,读门罗,似乎是在读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那些波澜不惊的故事背后,却有着生命强有力的张力。正如她在诺奖授奖视频中所说,希望“故事中有触动你的细节,这些细节让你在读完作品后感到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
在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上,面对具有鲜明现实特色的五部获奖小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表示,在市场的天平上,大众文化不仅是我们难以撼动的现实,也是战胜精英文化的强大武器。我们该何去何从?“最令人感动的是,今年的五部获奖作品居然不约而同地具有古典情怀,这与瑞典学院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不约而同。”
对于门罗的探讨还有一点,就是其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写作形式。而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素有重长篇、轻视中短篇的倾向,这与销量、影视改编等市场化元素密切相关。而以99读书人为代表的出版商,近两年进行的“短经典”系列以及今年的“中经典”系列,集中收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说集,也在这个重视大与多的时代,希望唤起人们对“小而美”的文字价值及“小而美”生活价值的关注。
类型文学 有待进阶
在与市场联系紧密的类型文学方面,今年最抢眼(也许并非仅仅今年)的人物还是郭敬明。在其执导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获得票房佳绩搅动了一番电影市场之后,其作品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论争也可谓精彩。通过在电影上的表现,在图书界早已被认知的“最佳产品运营经理”之类的称呼,也为更广泛大众所熟悉。当然年底郭敬明在图书领域也进一步显示着自己的营销能力,这在其推出反映十年心路历程的散文集《愿风裁尘》上可见一斑,限量明信片、“影像书”依旧展现着其营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