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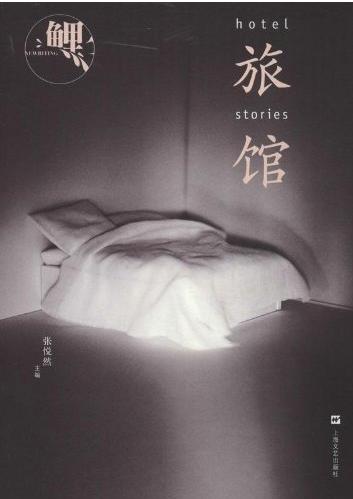 张悦然×颜禾 张悦然×颜禾
她曾为她的婚礼充当伴娘
颜禾是杭州女孩,从杭高考入浙大后,又作为交换生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书,成了和张悦然一个宿舍的舍友。“晚上我们都睡了,张悦然还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星座的书。她是个占星迷。”颜禾回忆。
新加坡的冬季时而阴冷。上课前,她们会先买一杯spinelli咖啡,握着温暖的纸杯,走入冷森森的阶梯教室。后来北京也开了一家这个咖啡店,马上唤起了两人的昔日情。
张悦然说颜禾的好处是忘性大,只有短暂的不开心,很快就能化解掉。
前年,颜禾在杭州举行婚礼,张悦然赶来当伴娘。颜禾和做出版的先生认识,也是张悦然牵的线。
【张悦然和她的闺蜜们】
颜禾、周嘉宁、张悦然,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最明显的标识不是文学,而是“高妹”。颜禾身高1米68,周嘉宁和张悦然都有1米7。采访那天,在北京百子湾艺术街区的一家咖啡馆。张悦然着平底鞋,长袖西装搭蓝色抹胸,浓黑长发,化了妆。随身带了一个英国小众品牌的女包,喜欢它是因为“没有LOGO”,“LOGO是不自信的东西”,她补充。颜禾活脱脱还是一名美少女,清爽的T恤短裤,素颜,笑时露出一对酒窝和大大的美瞳。摄影记者给她们拍照时,恍惚有拍时尚大片的错觉。
之前听闻张悦然性格有点傲,当面问她,她说:“也不是傲啦,是性格比较闭塞,不太擅长联络。”她承认平时跟出版社以及作者都欠交流,要向传统媒体学习,比如“《收获》的编辑会因为一个词的改动,认真讨论”。8月19日,她们在上海举行了一个西式晚宴,专门感谢帮助过她们的人,不善交际的女主编也开始学习成熟起来。
张悦然×周嘉宁
“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做《鲤》,我立刻说好。”
周嘉宁是上海人,翻译加创作已出版了七八本书。张悦然曾这样说起“新概念”,“要是没有这个比赛,我就不会认识这么多同龄的写作者”。这里着重指的就是周嘉宁。
两人的友谊在混文学论坛时生根发芽。“她一念大学就去了新加坡,我们就在黑锅、暗地、病孩子这些文学论坛玩。”周嘉宁回忆,那时文学青年都想办文学杂志。
对于那个已消失在时光深处,在新加坡的深夜与计算机编程作业鏖战的张悦然来说,黑锅和另外两个文学论坛,几乎是精神支柱。“如今想来,论坛时代是一段难忘的集体生活。”她这样定义。
一起做《鲤》似乎是水到渠成。“我还记得2007年12月31日,我跟朋友在上海一家咖啡馆,张悦然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做《鲤》。我立刻说好。”周嘉宁说,“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有什么事,第一个想到和她讲。这也是我们长期在工作中能够相处的一个原因。”
张悦然会在周嘉宁生日时送上体贴的跨洋祝福:“刚才占用你的电话线,陪你跨过了这几分钟,赖也赖不掉地走进新的时辰。生日快乐,亲爱的小bo”;也会不失时机地调侃周嘉宁的驾车技术:“bololo(周嘉宁的网名)小姐很得意地告诉我,她今天开车,竟然还没有熄过火”。
而张悦然30岁生日,收到周嘉宁用快递寄到北京的一幅画,是她亲自画的,画的是张悦然最爱的动物——猫,“画得真好啊,连今天下午的天气都画出来了!”张悦然不住赞叹。
三人新动向——
颜禾升级当妈
张悦然要去人大当老师
周嘉宁出了翻译新书
颜禾曾经晚上十点,被张悦然一个电话叫起来改封面。 “《鲤》的封面最多做过20多个版本。”
周嘉宁也和张悦然发生过争执:“我们之间的讨论都试图要说服对方,但这不是吵架。”
张悦然觉得自己很像三人中的管家,“各种操心”。“她们就像两只氢气球,我是块石头,在下面垫着。”
唯一不泯的是昔日的友情。
“去年因为我在别处,今年因为你有了宽宽小朋友,想来以后会有更多不能陪你一起过的生日。昔年在同住的幽仄公寓里,为你烘一只糊黑生日蛋糕,插起蜡烛蹭着你的寿星的喜气一起许愿的时光一去不能返。一去不返,但还停驻在那里。”
这是去年颜禾生日时,张悦然发的微博。
自从颜禾升级做了妈妈,张悦然也升级做了干妈,送了全套的小王子西装,还有拍照神器——一件婴儿全毛坎肩。
而张悦然的生活也有新动向。她正在创作一个和文革有关的长篇,“如果说文革对我们的父母一代是深刻的烙印,那么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这个烙印仍在延续。”9月份,她将去中国人民大学当老师,“开一门短篇小说的公选课”。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会不会第一堂课爆满,第二堂课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张悦然回答:“作家离开普通生活太久,我很害怕完全架空的生活。”
而周嘉宁上个月有一部翻译的小说上市,是美国女作家兼导演米兰达·裘丽的作品——《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紧接着又在豆瓣发布了电子书《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里面收录了她的四个短篇。其他两个闺蜜都在第一时间微博转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