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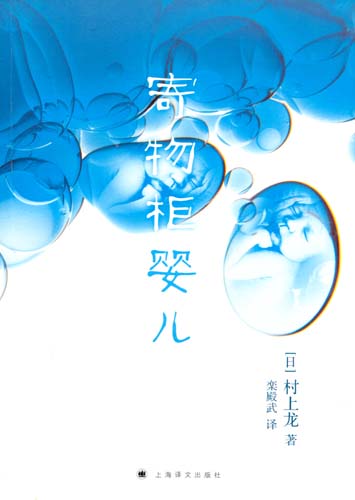 1999年,中国的年轻人中,骚动着“世纪末”不安与兴奋。 1999年,中国的年轻人中,骚动着“世纪末”不安与兴奋。
从书店到地摊,一窝蜂地热卖《上海宝贝》;70后80后书虫们,津津乐道于《挪威的森林》中的桥段,村上春树席卷了国内大小书店。
就在那时,另一个村上——村上龙也悄悄进门。漓江出版社引进了他的小说集——《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其中,村上龙用只有男生之间才会使用的放肆、露骨的语言,描述着血腥、污秽、放荡、暴力与噪音的场面。对于14年前的中国人来说,这显然过于“重口味”。
时过境迁。今年,浙江文艺和上海译文两大出版社,将村上龙的重磅代表作一部接一部地推向书市,4月底至今,在国内卷起一股凶猛的“村上龙旋风”。目前,这两家出版社正在积极促成村上龙来华。
回到2007年。白岩松赴日本进行《岩松看日本》的采访,村上龙成为老白在日本文化界选择的唯一采访对象。在对话的结尾,白岩松祝当时55岁的村上龙“永远30岁”。
这是因为,村上龙早就被世人视为为年轻人代言的“文化英雄”,他的作品里所散发出的叛逆、锐利、颓废与疏离,都是这个时代日本青年情绪的逼真写照。
1952年,村上龙出生于佐世保美国海军基地附近。他的家乡,不时被喷气机的轰鸣声所笼罩,空气中混合着花生酱、洋芥子、炼乳、煤油、古龙香水的特殊气味。
18岁到20岁之间,村上龙过着色彩强烈的青春:和兄弟们组织摇滚乐队,参加抗议美军核动力航母停泊的全国学生示威游行,入学半年不到即被美术学校开除。
往后20多年间,他以村上春树口中“鲨鱼一般的好奇心”,来回穿梭于日本社会各阶层与世界各地,用近乎速写的神妙笔法,勾勒眼底的浮生万象。
他用文字探索人性。1980年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婴儿》,描写两个被父母抛弃在寄物柜的婴孩,长大后如何人性扭曲并走向毁灭。村上龙因此作而被授予野间文艺新人奖,也因此被日本评论界拿来与大江健三郎相提并论。
他用文字书写充斥于现代社会的暴力与战争。《五分钟后的世界》虚构了日本在二战末期本土被攻陷的情节,日本在接近毁灭的边缘苦苦挣扎。
他用文字探讨富有情调的生活与恋爱。1986年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情爱在东京、纽约、巴黎这些大都会的舞台上开演,而美味佳肴和名贵洋酒,则成了这些舞台上最华丽的道具。
他用文字进行科学幻想。1982年村上龙完成了《别急,朋友》的小说与电影剧本,其中不仅有生物工程技术、克隆以及细胞工程技术,更有外星人出没。
他用文字折射日本社会的低迷、停滞与僵化,以及年轻人在无望大环境下的反抗。他的书中,常提到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当下流行的各种音乐和电影。
村上龙永远敏感地触摸着时代的核心,将社会脉动,转化成笔下一部部扣人心弦的奇异作品。小说中各种惊人素材,大多是他的亲身体验。而他笔下的主角,大多是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物。
“很黄很暴力”的坚硬外壳,包裹着一颗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柔韧内心。
“如果在这个社会的某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人,或者说是想要自杀的人,如果我的书对他有益的话,我觉得就很值得。”
他的笔下,那些不幸的悲观青年,最终都顽强地活了下来。村上龙用这种方式,给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一抹亮色。
有人把村上龙称为“日本的凯鲁亚克”,日本“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对这种说法的反驳,其实很无力。因为村上龙这辈子,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