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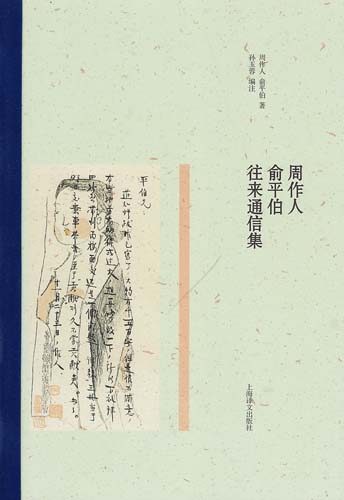 从1918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师从周作人,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他们之间有着近五十年的师生交谊。他们通信非常频繁,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从1921年3月1日的第一封信到1964年8月16日的最末一封信,时间跨度四十余年。 从1918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师从周作人,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他们之间有着近五十年的师生交谊。他们通信非常频繁,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从1921年3月1日的第一封信到1964年8月16日的最末一封信,时间跨度四十余年。
陈飞雪(以下简称“陈”):孙老师,您编注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年初出版以后,很快在读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兴趣。媒体上的消息、采访和书评等各路谈论很多,取向也颇丰富。周作人、俞平伯的书信,在他们各自的集子中都有所收录,但像这次完整地加以整理,并且按照往来时序编排,五百余条注释,详细的人名索引,可以说是一次集大成的工作。读者感兴趣的方面很多。想请您谈谈编注《通信集》的工作和细节。
关于周、俞两位的书信来源,我注意到您自己最常用的表述是“劫后余生”,能从这里开始和我们谈谈吗?
孙玉蓉(以下简称“孙”):好的。整理他们的通信,最为感慨的就是能够触摸得到时间的磨损,体会到这些信件保存下来的不易。大家都知道,从1918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师从周作人,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他们之间有着近五十年的师生交谊。他们通信非常频繁,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从1921年3月1日的第一封信到1964年8月16日的最末一封信,时间跨度四十余年。如果说书信从落笔就有生命的话,最年长的信已有九十多岁,最年轻的也近五十岁了。
俞平伯在1929至1932年间,曾分三次将周作人自1924年8月至1932年1月写给他的193封信,装裱成册,名为《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这就是《通信集》最为宝贵的来源。“春在堂”实为俞平伯曾祖父曲园老人的室名,俞平伯将《苦雨翁书札》冠以“春在堂藏”,无非是为了表示郑重。《书札》做得极为精美,感动得周作人也想把俞平伯的书信整理装裱,题目都想好了,曰《古槐书屋尺牍》。可惜被俞平伯阻拦了。此后俞平伯收藏的周作人书札,都在政治运动中被毁掉了,不然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通信集会更完整。“文革”期间,俞平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了“牛棚”,被抄家,“扫四旧”的大火把他的藏书、文稿几乎焚毁殆尽,厚厚的纸灰飘散在他的旧宅——老君堂寓所的院子里,损失惨重。然而,《苦雨翁书札》 三册却能幸免于难,这要感谢俞平伯的先见之明和珍念之心了。是他及早将 《书札》 交给儿子俞润民带到天津的家中保存,才躲过了那场浩劫。
陈:您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广泛征集俞平伯先生的书信,其后《俞平伯书信集》、《俞平伯年谱》、《俞平伯全集》 等相继出版,您或写作或编纂或主持。听说在历次运动之后,特别是随着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两家少有往来,九十年代初是您的寻访,促成了一次关键性的见面,周作人存俞平伯的书信得以发掘和整理。
孙:过奖了。事情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后期,我应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之约,搜集、编选《俞平伯书信集》。九十年代初,经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介绍,我与周丰一先生取得了联系。之后按照约定时间,陪同俞润民先生,带着三卷册《苦雨翁书札》到周家拜访。当周丰一、张菼芳夫妇看到保存完好的《苦雨翁书札》时,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不敢相信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还能有这样的奇迹出现。随后,周丰一夫妇应俞润民的要求,从周作人众多存信中,挑选出俞平伯的书信。这之后两家便为出版周、俞通信集而多方联系,才有了北图出版社《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以下简称《影真》)的出版。说到这里,不能不感谢鲁迅博物馆在“文革”期间的全力相助,使周作人所保存的史料免于劫难。
陈:有学者注意到《俞平伯全集》 中收入的致周作人书信只有94封,这次补到了181封。
孙:能注意到《俞平伯全集》收入书信不够全的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非常有意义。《俞平伯全集》出版于十五年前,那时的学术氛围还没有现在这样包容、宽松,家属仍然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当时的出版社经过慎重考虑,也做出让步,充分尊重版权所有者的意见,只将经过家属挑选的94封致周作人的书信,收入其中。这次可以说是尽其所有整理出版,要感谢各方面的支持。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必然进步。
陈:您能简要谈谈《通信集》和《影真》之间的关系吗?
孙:1999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影真》。2009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经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多方联络,征得周、俞两家亲属的同意,在《影真》的基础上,增补、编注完成了现在出版的《通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