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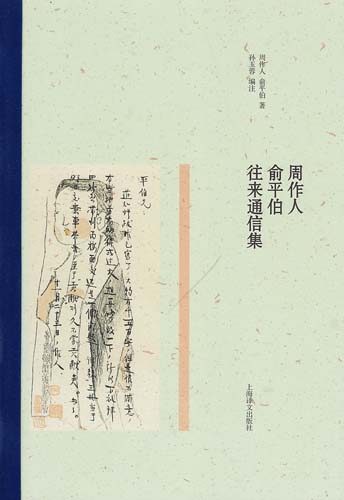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通信过去汇编成《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现在又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前者全部彩色影印;后者则为排版印刷,选配五十余幅彩色影印信笺用作插图。简单看来,两部书的区别似乎仅此而已;然而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通信过去汇编成《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现在又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前者全部彩色影印;后者则为排版印刷,选配五十余幅彩色影印信笺用作插图。简单看来,两部书的区别似乎仅此而已;然而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通信集》在内容上对《书札影真》有所增补,此其一。《书札影真》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全部影印自俞平伯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所装裱的三册《苦雨翁书札》,《通信集》在此之外又据《周作人书信》等出版物补充若干。《通信集》对《书札影真》中“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的增补则系首次揭载。周丰一、俞润民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中写道,保存下来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以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信为最多”。这回《通信集》所添加的,恰恰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居多(见右图)。
这些新增加的信件涉及不少俞、周二人当时的行事和想法,为我们素所不知。《通信集》编者就据此考证出俞平伯曾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先后在周作人担任社长的艺文社和艺文杂志社当过干事,为《艺文杂志》编审稿件(见《俞平伯轶事考订二题》,载《新文学史料》二○○五年第一期)。我也来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俞平伯:“昨买《绝俗楼我辈语》读之,殊不佳。”俞的复信已佚,不知当下如何说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氏为俞著《杂拌儿之二》作序,复云:“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龛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时隔许久,俞平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作人信中重又提及白采所著此书:“《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簏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贻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帧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太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謰謱矣。”对比俞平伯早年写的《与白采书》《眠月——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此番所言更其深切。而据此可知,周氏还为《绝俗楼我辈语》写过题记,即俞平伯所云“帧首数行”者,惜已亡佚,不知其详。
《通信集》在编排上对《书札影真》多予订正,此其二。《通信集》编后记写道:“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绝大部分信末未署写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无的信件,这给全书的编排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俞平伯收藏的三卷册《苦雨翁书札》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范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而俞平伯的书信都是散篇。在没有信封的情况下,判断写作年份的任务就尤其艰巨,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编者为此所下种种功夫最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订正的是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部分。其实《苦雨翁书札》排列也有错,譬如其中两封曾收入《周作人书信》,分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后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书札》的次序,系为“(民国)十五年”,《通信集》编者则据俞氏来信内容等线索判断出二信实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写。
《通信集》与《书札影真》有排印影印之别——本文开头已经提到,此其三。影印手札之类,至完成排序,编者工作已告结束,剩下的就是装帧与印刷了。排印则尚需一一辨认字迹。这项工作殊非易事,而且认对了不算功劳,认错了便是谬误。一字之差,意义可能相去甚远。且另举一个例子。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项下有云:“收伪北京大学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聘书,即复函接受这一聘任,并在当日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则云:“……当天的日记中却是这样写的:‘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二书作者应当是看过周作人日记的;因为正式印行的周氏日记只到一九三四年为止,以后他人著文涉及此事,均从前述年谱、传记,我写《周作人传》时也不例外。我的书出版后,承周氏后人告知,那段日记引用有误。待看到日记原件,该日的内容是这样的(原文无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