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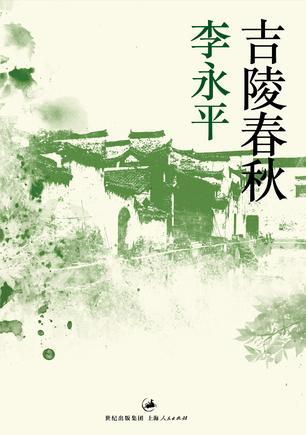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深受“五四”文学影响,如今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之一。近年来,李永平等一批马华作家的旅台文学引进大陆并受到关注。新一轮的华文寻根热潮再度掀起,作家们纷纷执笔追寻离散因缘的自觉意识被推至空前的高度。每一个置于边缘的海外作家,都有强烈的溯根愿望,都有大中华情结,李永平自然也不例外。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深受“五四”文学影响,如今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之一。近年来,李永平等一批马华作家的旅台文学引进大陆并受到关注。新一轮的华文寻根热潮再度掀起,作家们纷纷执笔追寻离散因缘的自觉意识被推至空前的高度。每一个置于边缘的海外作家,都有强烈的溯根愿望,都有大中华情结,李永平自然也不例外。
作为第二代婆罗洲人,李永平从早期的《拉子妇》、《吉陵春秋》开始,就给自己贴上了浓重的流亡标签。在《吉陵春秋》简体版序中写道:1976年,“我”以一个“南洋浪子”的身份,结束了在台湾的游学生涯,告别栖身的台湾,一路漂流,落脚美国新大陆。寥寥百十来字的开篇语,“浪”、“漂”、“流”、“栖”、“落”等离散味很浓的字眼频频闪现,我相信这绝非作家有意为之,而是试图通过一段意味十足的文字,牵引与“一本小说”有关的诸多因缘。
一场生平的第一场雪,降临异乡,从沙捞越到台湾,再到美国的奥伯尼市,渐行渐远的离愁,以及那块永远割舍不了的大陆,不会因为乌托邦式的浪游而湮灭。李永平书写《吉陵春秋》,竟然因了一场充满幻化色彩的雪:自然恩赐的精灵,呈现出的是“宁谧、美丽、白皑皑”的图画,在这背面,却是一副“鬼魅似的,阴森森”的绚烂意象。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画面,始终在李永平的作品中交织。那个写进简体版序的“老婆婆”,就是这部小说的因缘所在,也是全部故事的玄机所在,现实带来的刺痛,让作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她从何处来?往哪里去?她背上那个鲜红的沉甸甸的包袱,里头装着什么东西,隐藏着什么秘密?她有没有亲人?”那个记忆中踽踽独行的老婆婆,便是整个吉陵灵异的化身,也是解读婆罗洲的唯一入口。
《吉陵春秋》由白衣、空门、天荒、花雨四卷组成,每卷又由三个小章节构成,每个小章节结构紧凑,收尾自如,独立成篇。小说一开始,作家呈现了一幅流年画卷,故事人物围绕棺材铺“啊咿出场”,从清纯美丽的长笙,到铺主刘老实,再到孙四房、春红、祝家妇人,其间又夹杂着算命的、收破烂的、赶骡子的、坳子佬、老道师、后生小子、胖妈妈、老爹爹、娼妇老鸨等各色人物,风月、风情、风华、风物……统统搬到万福巷这个无比鬼魅的舞台上,并逐一批算。“万福巷”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人物的命运由一桩奸杀案牵引而来,由“报应论”主导的叙述之轴缓缓地拉开。
世代饱尝战争离散的辛味,到了李永平这代又长期遭遇大陆文化的遗弃,于是他不得不孤守一隅召唤母体,少妇、少女、老妈妈,个个诡秘香艳,他笔下的女性都活在了色彩浓烈的诅咒之中,宿命的标签处处警醒着,“天上有雷,地下有阎罗”、“冤有头,债有主”、“那对蝴蝶是一双薄命夫妻,如今给十一害死了,天打雷劈,要受报应哟”……这样的“报应”旋律始终贯穿于氤氤氲氲的香火清烟里。
当年博尔赫斯说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让你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阅读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也同样有这种压抑感,那些人物之间的搏斗,道德的拷问,人性的复杂纠结,让人拥有欲罢不能的痛感。
有人给《吉陵春秋》定义为“红楼笔法”。我相信《吉陵春秋》的渊源在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那里。这并不意味着李永平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他受过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在观点、方法上与大陆作家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和升华,这使得个人自觉的努力更加有效。他的写作姿态,是对大陆长期漠视文言小说,使生动、精练的半白话语言处于半盲状态的有力反讽,同时对五四时期林纾主张“古文之不宜废”的观点给予了正面支持和实践。
在《吉陵春秋》中,作家对语言的打磨非常值得细啜,这得益于李永平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方言俚语的运用,以及对语言陌生化处理和极端实验的勇气。比如小说第119页,有这么一句话:“二十一岁那年,他穿了一身标骚的学生制服,把一张白削的脸皮刮得亮堂堂。”“标骚”一词可谓神来之笔,活脱脱将一个纨绔少年的形象呈现了出来。
真没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李永平就已经令人吃惊地写出具有原乡意味的《吉陵春秋》,这是一块由无数个吉陵接壤的巨大原乡,那就是中国。
“人终究是要回家的。”现在,李永平已经回来了,驻足于每个华裔读者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