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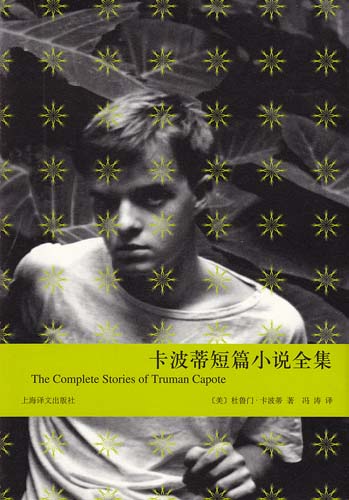 读这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生出了好一些感叹:集中17个短篇小说(因版权原因,《圣诞忆旧》等三篇只有存目没有内容),15篇写于杜鲁门·卡波蒂十几二十几岁时。《冷的墙》最早,1943年的作品,那时,卡波蒂只有19岁——当然,他写作生涯的开端还要远早于此——倒数第二篇《通往伊甸园的小径》写于1960年,小说主人公艾弗·贝里已经55岁了,依旧春心荡漾,而作者卡波蒂正值壮年,已经写出了《蒂凡尼的早餐》,风头正健。5年后,长篇小说《冷血》,将卡波蒂的创作生涯推至巅峰。再后来,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在创作上,卡波蒂走了差不多二十年的下坡路,笔头枯涩。这个时期,收入《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的,只有一篇《莫哈维》(1975年)。在写于22岁的短篇小说《无头鹰》中,卡波蒂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主人公文森特自认是诗人,但从没写过一行诗;自认为画家,但从未画过一幅画,“哦,他并非没有尝试过——开端总是不错,可结果总是很糟”(第121页)。最后那句话,似乎可以拿来做卡波蒂这一生的批语:“开端总是不错,可结果总是很糟。”卡波蒂,以及我们所有人,想要追求的自然是圆满,谁欲落入虎头蛇尾的怪圈?卡波蒂的晚境,表面上看看似乎还有些灿烂,内里却早已腐败,不能不说是很让人悲哀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说,这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在作家生命的经纬度上,大体上是处在“总是不错”的地方,《通往伊甸园的小径》是成熟期作品,描写上流社会的《莫哈维》虽给人以萧索之感,但里面的卡波蒂,依旧清醒老辣。 读这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生出了好一些感叹:集中17个短篇小说(因版权原因,《圣诞忆旧》等三篇只有存目没有内容),15篇写于杜鲁门·卡波蒂十几二十几岁时。《冷的墙》最早,1943年的作品,那时,卡波蒂只有19岁——当然,他写作生涯的开端还要远早于此——倒数第二篇《通往伊甸园的小径》写于1960年,小说主人公艾弗·贝里已经55岁了,依旧春心荡漾,而作者卡波蒂正值壮年,已经写出了《蒂凡尼的早餐》,风头正健。5年后,长篇小说《冷血》,将卡波蒂的创作生涯推至巅峰。再后来,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在创作上,卡波蒂走了差不多二十年的下坡路,笔头枯涩。这个时期,收入《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的,只有一篇《莫哈维》(1975年)。在写于22岁的短篇小说《无头鹰》中,卡波蒂创造了这样一个人物:主人公文森特自认是诗人,但从没写过一行诗;自认为画家,但从未画过一幅画,“哦,他并非没有尝试过——开端总是不错,可结果总是很糟”(第121页)。最后那句话,似乎可以拿来做卡波蒂这一生的批语:“开端总是不错,可结果总是很糟。”卡波蒂,以及我们所有人,想要追求的自然是圆满,谁欲落入虎头蛇尾的怪圈?卡波蒂的晚境,表面上看看似乎还有些灿烂,内里却早已腐败,不能不说是很让人悲哀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说,这部《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在作家生命的经纬度上,大体上是处在“总是不错”的地方,《通往伊甸园的小径》是成熟期作品,描写上流社会的《莫哈维》虽给人以萧索之感,但里面的卡波蒂,依旧清醒老辣。
17篇小说,题材多样,有美国南方乡村故事(《银瓶》、《过生日的小孩》等),也有纽约哥特风灵异故事(《米丽亚姆》、《无头鹰》)。风格上也有区别,上述前一类小说的起承转合非常讲究,后一类小说情节则比较松散,有时还会出现长段的意识流描写(《无头鹰》),多能体现作者本人的心绪。《关上最后一道门》和《圣诞忆旧》,是我最喜欢的卡波蒂短篇小说,后者大概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关上最后一道门》(1947年)讲了一个无能的感情骗子的故事:沃尔特,又一个去到纽约的穷小子,先是撬了好友的墙脚,进而找了个富家小姐。竟然还不知足,又和小姐的闺蜜打得火热!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谁想到,不过是在报纸上炫耀了一下与那小姐的关系,良辰美景都倒塌了。小姐不要他,回头找前女友又被“打枪”,闺蜜还对他说:“沃尔特,你听我说:要是每个人都不喜欢你,都跟你作对,别以为他们是蛮不讲理;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实在受不了,他跑到乡下去,蜗在一家汽车旅馆中,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的风扇旋转,悟到这样的道理:“没有一样东西,沃尔特,是表里如一的。圣诞树是赛璐玢,雪花也不过是肥皂片。在我们体内四处飞翔的是一种叫做灵魂的东西,你死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死;没错,我们活着的时候也压根儿没活。”沃尔特,不就是那落入“开端总是不错,可结果总是很糟”怪圈中的人儿吗?
卡波蒂属于他自己曾经称道的那种“风格化作家”,不同的篇章之间,总有什么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字里行间永远有一股子喜乐,但转眼间美丽就要陨落,常情就要迸裂。而促使这种危情发生,或许不过一根稻草的重压。借用法国同性恋作家让·热内的一个意象,卡波蒂的女角,都是“鲜花圣母”一类的人物:希冀能普照众生,最后却常让人觉得在笑着流泪。最典型的,莫过于《过生日的小孩》中那个小姑娘博比特“小姐”以及《蒂凡尼的早餐》中鼎鼎大名的霍莉·戈莱特利小姐。“圣母”的世界,充斥着恶毒忿恨——仿佛恶毒的诞生,完全只因圣洁的存在太过明亮,非得调和一下不可;仿佛这圣洁,才是最大的恶——这是我认为卡波蒂所揭示的最残酷的事情。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卡波蒂笔下的“恶”,不过小打小闹,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另一个令我感叹的地方在于:天才作家,到底还是有的,绝对不是什么神话。读卡波蒂二十出头写的那些小说,我时常赞叹其观察之精细,叙事之流畅,譬喻之巧妙。如果只能举一个例子,我会举《无头鹰》开头那段对七月城市的描写。不过,读了《巴黎评论》1957年对卡波蒂的采访后,我又想起了那句老话:天才,其实是培训出来的。《巴黎评论》的采访者帕蒂·希尔问卡波蒂:是否存在提高写作技巧的利器?卡波蒂回答说:“据我所知,多写是唯一的利器。写作具有关于透视、影调的诸般法则,就像绘画或音乐一样。如果你生而知之,那很好。如果不是,那就要学习这些知识。然后将它们以适合你自己的法则重新编排。即便是我们那位最傲慢的乔伊斯,也是个超级工匠;他之所以能写《尤利西斯》,是因为他能写《都柏林人》。”(黄昱宁译,《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Ⅰ》中译本第4页-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