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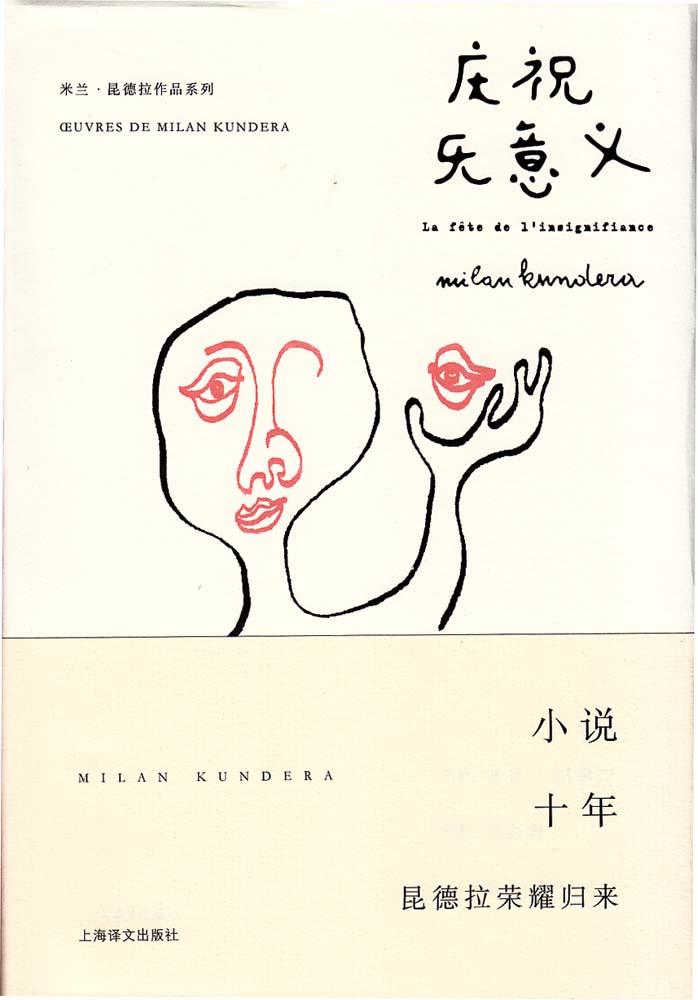 杜鲁门·卡波蒂写《应许的祈祷》写得异常艰难。基本上是编辑催稿,他就写上一点,否则就兀自磨洋工,愣是把这本书的写作从上世纪60年代拖到80年代,而且最终没有写完。卡波蒂动笔时声称要写一部堪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杰作,结果天不遂人愿,仿佛正应了那句谚语———大山临盆,生下来的却是一只小耗子———卡波蒂阵痛十来年诞下的这本《应许的祈祷》,离《追忆逝水年华》差得可不是一点点的远。 杜鲁门·卡波蒂写《应许的祈祷》写得异常艰难。基本上是编辑催稿,他就写上一点,否则就兀自磨洋工,愣是把这本书的写作从上世纪60年代拖到80年代,而且最终没有写完。卡波蒂动笔时声称要写一部堪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杰作,结果天不遂人愿,仿佛正应了那句谚语———大山临盆,生下来的却是一只小耗子———卡波蒂阵痛十来年诞下的这本《应许的祈祷》,离《追忆逝水年华》差得可不是一点点的远。
这本书也让卡波蒂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书中的三篇作品,《原姿原态的怪物》、《凯特·麦克劳德》和《巴斯克海岸餐厅》,曾分期发表于1976年《时尚先生》杂志。文章一出来,就令上流社会大为震惊:卡波蒂将他长期厕身、融入、观察的这个社会的诸多不堪入目的光景,以纪实的方式向外界抖落了出来。作为报复,上流社会驱逐了他,而卡波蒂本人,这个一度被其娇宠、吹捧、纵容的花儿一样的文学小王子,蔫了,老了,堕落了,最后沉沦于醉酒和毒品中,直至1984年去世。
卡波蒂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些文章可能会惹来的麻烦,但他还是过于乐观,在《凯特·麦克劳德》的篇首他写道:“我也许是一只害群的黑羊,但我的蹄子却是金子做成的。”这种自信恰恰是那些年少时一书成名,然后靠着一众粉丝你来我往互点“关注”、并指望着成年人耸耸肩不介意他小打小闹恶作剧的侥幸心态。但一只羊就算蹄子真的是金子做的,被践踏的众多老少也未必真的乐意去舔这只蹄子。一言以蔽之,在世俗人情上,卡波蒂太愚痴,太顽劣,也太幼稚了。
当然,这种幼稚为我们带来了一组“原姿原态”的人物速写。主人公、文学菜鸟P·B·琼斯以时而坑蒙拐骗、时而贴肉卖身的方式,融入并见识到这样一个顶级俱乐部,此中的男男女女可不像我们在电视上、杂志上看到的那么光鲜亮丽:葛丽泰·嘉宝可以毫无忌惮地说荤段子,威廉·福克纳是个黄汤不离身的酒鬼,萨特“外斜眼、面容白如馅饼”,他那“老处女似的姘妇”波伏瓦像个“被扔弃的玩偶”,萨缪尔·贝克特一边装清纯一边做富婆的小白脸,杰姬·肯尼迪像从”伪娘时装大赛“走出来的易装男……还有许多过气的或者从来没来过气的人。卡波蒂通过比喻、联想、类比,寥寥几笔就把他们的外在和内心表现得栩栩如生,而他的挖苦、揶揄、讽刺使整本小说跳动着一种机智、谐谑、恶搞的风格,结构上极尽线索繁复、时空错位之能事,叙事语言则如机关枪出膛那样快、稳、准、狠。
但,这仍然只是一组成功的人物速写,而不是成功的小说。纵观卡波蒂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他的心理年龄总有一部分停滞于那个时而作恶、时而做梦的男孩阶段,他的笔下也尽是些亦仙亦妖的童话式人物。他的处女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写男孩灵与肉(同性恋)的成长和觉醒,《草竖琴》(1951)写老法官和老姑娘上树,《蒂凡尼的早餐》(1958)写品位不凡但没钱的穷姑娘如何甩手腕钓男人,然后在商店顺手牵羊做贼骨头。这些作品洒脱、轻盈、率直,充满一种毫不做作的优雅与放荡,既塑造了当年的卡波蒂,也定义了他笔下的一代美国青年。
然而,《应许的祈祷》却失掉了这些风格。就像40岁的男演员想到自己再也无法涂脂抹粉地去扮演十七八岁的小伙子,40岁的卡波蒂也意识到个人有限的人生历练无法为创作开拓新的空间。因此,他花大把的时间去研究他人的生活,最后有了一生创作的顶点———非虚构作品《冷血》(1966)。
但是当他重新回归小说写作,他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应许的祈祷》涉及上述提到的几种作品主题:成长、自由、性爱、心灵的禁锢与解放,以及一伙亦仙亦妖的人与事。但是,卡波蒂为了让自己显得老练,以至于在行文上巧作卖弄,其刻意与矫情“虚高”了作品的调子,就像一个青春期男孩竭力装深沉,却让他的破锣样的变声期嗓子出卖了那样不自然。
比如,关于性,卡波蒂早期作品中半藏半掖的同性爱、多P等情节,经由他哥特式、怪诞化的处理,总能取得一种别样的效果,但在本书中,卡波蒂的文笔却甩脱了镣铐而奔向了“自由”,用词直接、大胆、露骨,却失之粗俗、戾气、下作,就像老男人炫耀性经验那样浅薄无聊。因此,在“男色家”这个身份上,他远没有达到他的日本同行三岛由纪夫的美学水准。至于挖掘名人隐私,他更只满足于窥阴,为毒舌而毒舌,而不像英国作家毛姆那样毒舌中自带“理解之同情”的暖色调,给予笔下的人物深刻的体谅和怜悯。除书中少数情节之外(如琼斯帮人捡起掉落的色情图片,却被对方羞愤莫名地含泪责备),卡波蒂大抵没有参透人性的复杂与幽微,这是非常明显也是非常遗憾的。更要命的是,这种“僵而不熟”的缺陷又沾染上末流“垮掉派”小说的习气,《应许的祈祷》中的人物但凡有一点不顺,就卖身、乱搞、酗酒、嗑药,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发一点感叹,全然没有卡波蒂上述早期小说中洋溢着的自自然然的朝气、灵气和邪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