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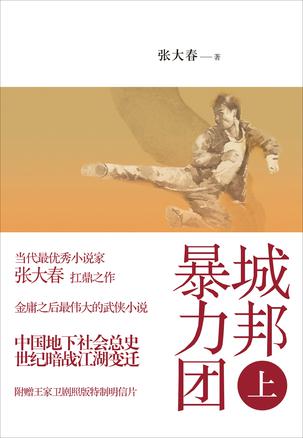 “张大春,华语小说家,山东济南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 ”这是百度百科对张大春的介绍。而照他本人的自述:“我大部分的力气花在重新认字、学着像我从小听到的说书人那样说故事、学着写旧诗这些事情上。 ” “张大春,华语小说家,山东济南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 ”这是百度百科对张大春的介绍。而照他本人的自述:“我大部分的力气花在重新认字、学着像我从小听到的说书人那样说故事、学着写旧诗这些事情上。 ”
他坚持每天写书法,每天创作一至六首旧诗。他把中国传统的笔记、说部、说书、章回和戏曲糅合在自己的小说创作里,又为一双儿女“重新认字”,让中国文字最终回到孩子们的生活情境。他还在台湾一家电台做了十年的说书节目,从《江湖七侠传》一直讲到《水浒传》……正因为此,当有人问“你是不是有意重拾中国传统”时,张大春迅速回答:“我没有重拾。因为我一直没有丢掉过。 ”
解放周末:谈到传统,我们似乎比较常说的是 “保护”、 “继承”,但您给我们的感觉却是在传统文化中进进出出,玩得不亦乐乎。
张大春:老是在 “捍卫文化”、 “保护传统”这样的层次上说传统,我不大认可。我们说的传统,如果是 “走路要守规则、不要闯红灯”一类的,那意义不大,因为这只是 “规矩”。对我来讲,这些所谓的旧学也好国学也好,它们从来都没有真的离开过我们,刚才说 “捍卫”、 “保护”,光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太 “传统”的概念了。
解放周末:我们生活在传统中,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大春:传统是无法割裂的。我们要先确定,我们并没有离开过传统,然后才去想,不管是创作活动,或者是生命活动,究竟在哪些范畴里是可以用和传统对话的方式来理解的。
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本 “书”。它上面有书法,也有很大块的留白。你可以把它当笔记本来用,可是它又有供人欣赏的功能,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和传统无关的东西。你在上面做数学题、画画、记一些悄悄话、打草稿,只要你拿起笔来在纸上写,那就是在传统中了。你要进入传统多少,是纯粹欣赏的层次,还是实践的层次,就在于你自己了。
解放周末:但日常书写现在也在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打字、按键。
张大春:确实是,现在钢笔越做越贵,字却越写越少。我不知道书写最后会不会被按键取代,但起码我知道,按键,不管是在键盘上还是屏幕上,都是没什么艺术可言的。
就我个人而言,走在路上尤其是商业街上,我会注意到各种招牌,会留意是电脑字还是书法字,是手写的还是制式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是我生活中念兹在兹的事。有的人非常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衣服是不是搭配得体,腰是不是粗了,白头发太多,黑头发太少……每个人在意的最表面的层次都差不多,可是再往里呢?很多人不见得在意自己是否能够文从字顺地好好讲话。现在去美容院的人很多,想办法把话讲对的人很少。人的容颜是没有什么传统可言的,但是你的语言、你的思考,你认知世界的能力,都需要文化累积,这种文化累积是多方面的。
解放周末:所以您持续不断地在累积,在耕耘。
张大春:其实我会的东西很少,很窄。我在四十岁以后慢慢发现,我本科、研究所时候很多该念的书都没有念。比方说 《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大学时候都没有仔细看,大概就看过两三篇。 《伶官传序》会背,但整个 《伶官传》没有看。所以大部分都在回头补。
解放周末:怎样发现哪些书是该念的,哪些其实不用念?
张大春:很多人问我怎样的书是好书,让我推荐书目,但我不推荐。很简单:你需要的书,最好没有实用价值。我的意思是,尽量在大比例的范围内不要抱着即学即用的心态,比如怎样挣钱、赢得地位、掌握权力等等,一般性的世俗的目的尽量不要放在阅读活动里面,这样我们养成的阅读习惯会比较好一点。
解放周末:您的阅读习惯似乎受家庭影响很大?
张大春:我从小跟着父亲在家里读书,我父亲喜欢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受家里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我的小孩却不受我影响,这一代孩子已经有相当大的自主性了。
我儿子学钢琴和小提琴,我女儿学钢琴和长笛。我也知道他们不可能走上演奏家的路,但我希望这成为他们终身的嗜好,起码是终身的兴趣,所以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的学习。而且,我儿子现在更喜欢建筑和篮球。满脑子是NBA,讲到哪个球星,职业生涯、进球纪录等等,都了如指掌。我对他产生不了实际影响,他看起来不会走我的路。
解放周末:子不承父业,会不会有点遗憾?传统文化又少了一个潜在的爱好者。
张大春:我父亲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期许,我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