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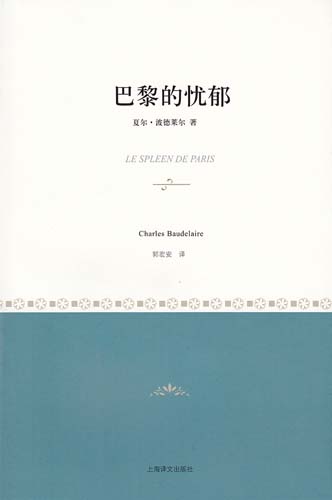 【孤傲的沉沦】他的“颓废”打开了“审丑”之门 【孤傲的沉沦】他的“颓废”打开了“审丑”之门
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起波德莱尔,也将其抬在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称其为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第一个现代主义诗人。我初次接触到波德莱尔也只是因为无意间得到了一本《巴黎的忧郁》,而这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又了解到原来此人竟有如此之大的名气。
曾经听说有人将诗歌与诗人分为重要而优秀的、不重要而优秀的、重要而不优秀的、不重要而不优秀的几类,我想波德莱尔大抵应该属于重要而优秀的那一类了。“重要”的指向应该是诗歌的历史性,而“优秀”应当是艺术性了。对于历史性,众人已经将其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而对于艺术性,恐怕多数的现代派对于波德莱尔的严谨的诗歌结构不屑一顾,当然我也可以从时代的角度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辩解,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对波德莱尔的诗歌予以自己的审美判断,而旁人绝无权力评价对错。更悲剧的是,如果你并不通法语,从译著去了解原著大家应该也知道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就好像戴着墨镜看熊熊燃烧的太阳,或许也能体会到耀眼之光芒,但终究对于光芒的领悟差了一层近距离的接触。
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波德莱尔的“颓废”或者“颓废主义”成为了他诗歌最重要的标签,而也有人说是波德莱尔第一次为文学艺术打开了“审丑”之门,这一点也坐实了波德莱尔对于象征派的先潮意义。这似乎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德莱尔的一生必定是潦倒困苦而一如曾经有学者将其比喻为法国的杜甫,当然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波德莱尔自己曾说,从童年时期便有孤独感,这当然与母亲的改嫁并将自己寄宿的情况有关,波德莱尔甚至将此理解为宿命。当把自己的孤独感受如此理解时,生命便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悲剧色彩--一生都拼命的抗拒孤独,而一生却又不得不行路在孤独之中。这又好像我们人类与死亡的关系,一生都为了寻求更好地生存,而却终将走进坟墓,那么一个人,他每日与死亡相对,必定是可怕而可怜的。这却又好像波德莱尔与孤独的关系了。到了这种情况下,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则被培养出来了。一种孤芳自赏、自我玩味的态度,一种因为被分离而诱发的纯粹的骄傲。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人,例如小说家之类,他必定是一个观察者。而诗人却略有不同,在观察的时候他必定要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甚至有时候观察的对象就是自己。在对世界、对自身解构时,意识在原始的符号中穿梭游动,有时变幻成为手术刀,将自己架在手术台上,内脏躯体四散剥离。在这时,波德莱尔用自己观察者的眼睛去解剖,用自己行为者的眼睛去流泪;他甚至用自己的左手狠狠的剁向自己的右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波德莱尔,我们则可以对波德莱尔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
波德莱尔很长的一段时间(或者说是绝大部分时间,甚至他临死之前)都在为法郎而奔波劳碌(虽然与母亲的关系分分合合,但是他的母亲从没有终止过对波德莱尔经济援助,母亲应该是波德莱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有理由相信,《恶之花》的结集出版应该与波德莱尔的经济拮据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波德莱尔试图通过这一手段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予以改善,同时能够清还自己的债务。但是即便如此,波德莱尔对自己的形象仍然是一如既往的苛求,“带有一种英国式的简洁风格”,而“他的恭敬的举止常常近于做作的程度”。从这一点我们似乎也可以从波德莱尔诗中的那种拘谨的格式中有所斩获,而他对人与社会的反常性的理解和演绎似乎就更加能够来自于自己的生活状态。
【浪漫的升腾】忠于本性的抒发化“丑”为“美”
写到这里,我更想谈论一下有关《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自己在序言中提到,他的这部散文诗集是充满诗情,富有音乐美,没有节奏和韵律,文笔灵活而刚健,正适合心灵的激荡、梦幻的曲折和良心的惊厥。这或者是波德莱尔从另一种方式之上对于自己生活的挣脱。这也许仅仅只是波德莱尔一种尝试罢了,但是他却能从这里得到一种适合自己心灵激荡的方式,这种更加自由的文体或者才能够更加适合波德莱尔对于从另一个角度对于美的抒发。当然,在这里,美代表着一种文学含义。
很难说清浪漫主义抒情的方式在波德莱尔的心中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哪怕他确实对雨果不是一般的崇敬,或者也是对雨果的高产有一定程度的敬意。当然,对雨果的赞美中提到的广度上无人能及有人认为这是意味着波德莱尔对于雨果诗歌的深度有一定异议。从这里看则比较有意思,一方面对于浪漫主义抒情抱有强烈的崇敬,一方面却对它的一些不如人意之处暗含影射(似乎就跟当前中国的一些名家所说的,真正的大师必须有所扬弃的继承传统,同时对先进的理念有所发扬)。他说真正的诗人必须孜孜以求的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而不仅仅只是描画看到的,这恐怕也正是波德莱尔求变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