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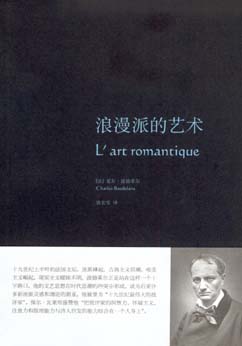 诗人在商业时代如何生存?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做书商?白天辛苦打工晚上写诗?还是进入体制内当个专业作家?诗人波德莱尔的例子或许可以为徘徊迷茫的文艺青年提供借鉴。这位19世纪象征主义诗歌开创者虽然一生负债,把自己忧郁迷人的面孔硬生生摧残成谢顶和酒糟鼻,但考虑到他数量惊人的开销(2400法郎的年金,政府副部长的年收入都不够他花),他所推介的生财之道总还是可靠的。 诗人在商业时代如何生存?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做书商?白天辛苦打工晚上写诗?还是进入体制内当个专业作家?诗人波德莱尔的例子或许可以为徘徊迷茫的文艺青年提供借鉴。这位19世纪象征主义诗歌开创者虽然一生负债,把自己忧郁迷人的面孔硬生生摧残成谢顶和酒糟鼻,但考虑到他数量惊人的开销(2400法郎的年金,政府副部长的年收入都不够他花),他所推介的生财之道总还是可靠的。
这条道路就是——写文学批评。
《浪漫派的艺术》一书,就是波德莱尔一生批评文字的集锦。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印象式批评,针砭时弊、论争文学,还有即兴而来的幽默,一看就知道是刊登于报章上的时评。
工业革命之后排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加上法国的沙龙文学传统,为报章批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文学的价值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波德莱尔就是这样一个卖文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他的书评有不少是评论当代人的作品,比如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评雨果的《悲惨世界》。
在波德莱尔看来,卖文为生可以使自己摆脱家庭的束缚和供给,更不用像法国古典作家那样取悦于自己的庇护者。因此,商业文化反倒成了独立自主的保障。在《给青年文人的忠告》中,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道:“文学建筑师应该不计价格地出售他的货物,因为仅有其名并不是一种获利的机会。”
不过,波德莱尔毕竟是一个诗人,跑来写散文,就像名演员客串小角色或者话剧演员拍电视,终究风范不同。在波德莱尔的批评中,充满着作家的个性以及他的文学创作观念。他虽然从诗歌的圣殿走下来充当文学批评的绿叶,却不会“为了窑户的一块田”而“出卖缪斯的文笔”。
相对于需要精心锤炼的诗歌,批评创作以其字多量大维持了诗人的日常之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诗人批评随着商品经济和报业流通日渐发展,源远流长。法国文学理论家蒂博代将之归入“大师批评”,而苏珊·桑塔格则在《诗人的散文》中指出:“自浪漫主义时代以降,大多数真正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是诗人。”天才如波德莱尔,理所当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