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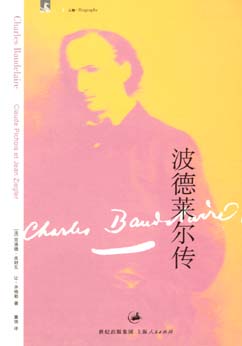 一般来讲,任何一位爱好文学或曾经爱好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酷爱波德莱尔诗歌的阶段。这位深深意识到自己绝不取悦所有读者的诗人,其实是最具普遍性的作家之一。 一般来讲,任何一位爱好文学或曾经爱好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酷爱波德莱尔诗歌的阶段。这位深深意识到自己绝不取悦所有读者的诗人,其实是最具普遍性的作家之一。
如果我们不去想那些表面上过于奇特的意象,如腐尸、蛆虫、红发女乞丐,撇开那些显得沉湎于肉欲的主题,如香味、乳房和女人浓郁的长发,又对人们并不一定去尝试的一些经验如抽鸦片忽略不计,再除去那些具有深厚基督教色彩的渎神层面,那么,一个具有基本感性的读者无不会对波德莱尔笔下和谐的黄昏和都市的忧郁感到一种共鸣。夕阳西下时一丝莫名的惆怅,一旦到了不可排解之处,便是波德莱尔式的;中学生瞒着父母偷尝一枝雪茄,乃至一枝香烟,是波德莱尔式的;少男少女往头发上抹一点发胶,将头发染成黄色,是波德莱尔式的;从初次与社会接触时遇到的头一次苦涩体验,到成年时候的彻底幻灭,都是波德莱尔式的。
波德莱尔的诗歌,具有一种人与世界初次交锋时激发出的全部个人意识的强度,是个人在人生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获得某种经验之后突然瞥见的自生至死的人生全貌,是个体在走出自己身体的躯壳而遇上世界的躯壳时灵魂的震颤与肌肤的战栗。波德莱尔诗歌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具有人在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乃至宇宙中的位置时所能揣测到的全部智性与感性空间的深度与广度。它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会一下子罩住我们,因为它与我们的整个世界同形、同疆域;会一下子照亮我们,因为它同我们的内心与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同样深邃、同样无垠。
波德莱尔之所以会影响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叛逆者,同时又能让成熟了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思考存在问题时不断进行参照,正是由于他的诗歌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体验感和广博性。
然后,会有那么一天,波德莱尔的世界仿佛一下子远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好像越过了“波德莱尔阶段”。他的作品开始与其他伟大的文学遗产一样,进入内心深处的某个图书馆中,不再具有笼罩一切的魔力。至于如何越过的,每个人又都会有自己的妙悟……也许是人们所说的“心灵蒙尘”;也许是生活走上了“正轨”;也许是生活沉重的质感,让人在忘却“浪漫”、失去抒情的状态下,同时带走了波德莱尔的世界。
而一个深深受到中国恬淡文学陶冶的文学爱好者,则会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学参照下,渐渐偏离《人工天堂》和《恶之花》作者充满荆棘的灵魂探索道路。在静观浮到客观世界表面的美的同时,我们必定会远离灵魂深处的深渊,在这一时刻,东西方美学的差异,就会深刻地影响到每个人的文学欣赏趣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究竟与波德莱尔同行,还是将其束之高阁,是检验一个人对生命感悟的深浅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在东西方美学观与艺术观中进行选择的一次考验。
(节选自《波德莱尔传》译者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