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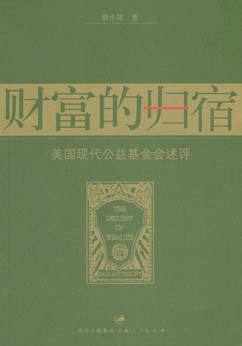 内容提要: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思想渊源,一种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宗教提供的慈善服务对扶贫济困、社会救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慈善也促进宗教教化功能的实现。随着社会分化,慈善和宗教逐渐分离,现代慈善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但宗教慈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宗教与慈善都面临着角色定位和社会管理的挑战,如何合理自我调适,回应社会的需求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内容提要:宗教是慈善重要的思想渊源,一种重要的慈善组织形式,宗教提供的慈善服务对扶贫济困、社会救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慈善也促进宗教教化功能的实现。随着社会分化,慈善和宗教逐渐分离,现代慈善注入了更多的内涵,但宗教慈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宗教与慈善都面临着角色定位和社会管理的挑战,如何合理自我调适,回应社会的需求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宗教是慈善的重要根源
总体来看慈善事业大体上有三个基本的源泉:慈善传统、人道主义传统、宗教传统;在当代又汇入了环保传统和人权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组织形式。在传统社会,其他组织性社会机制并不发达,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公共责任都很小,宗教组织是社会中很少的能够提供组织性慈善事业的社会机构。宗教团体的组织网络,较高的社会公信力使宗教组织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在政府、家族、行会之外,往往都由宗教团体提供。宗教慈善活动可能是唯一持久和经常性的慈善活动。宗教的组织性慈善也可能是传统的慈善过度到现代慈善的节点。如果把宗教的目标抽象到普济、普渡、普觉的层次,[①]我们会发觉,宗教和传统的慈善有许多的共同的东西,乐施好善、悲天悯人、扶危济困都是宗教和慈善共同的东西,不同的宗教也都把施善和回报作为达致其他层次的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与慈善是同源的,或者说灵犀相通。西方扶弱济贫的传统主要源于《圣经》的教导,伊斯兰教“敬主行善”的观念也强调施恩于人。就中国的史实来看,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布施的概念,转化为后来的救济观念。梁武帝时期,在建康设立“孤独园”恤养孤儿和贫穷老人,这些工作后来在宋代演变为佛寺的悲田养病坊,后被政府所接收,也被民间善男信女所仿效。宗教和慈善都有另一个共同目标:教化。台湾学者梁其姿经过梳理中国两千多种地方志统计:16-19世纪明清时期,中国有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339个、清节堂216个、施棺为主的慈善堂589个、综合性善堂338个,其它慈善团体743个。[②]这些善举不是单纯地要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事实上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借施善去尝试重振社会秩序,重点在于社会等级的重新界定;诉求往往带着浓厚的道德性。慈善济贫纯粹是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价值。重视孝道与贞节、蒙学教育、儒家正统的葬礼、惜字积德以增加科举机会。与慈善异曲同工的是,宗教的重要功能也是教化。美国早期大学历史与慈善捐助是关联的,不同教派支持成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学生的选择也多限于本教派的教徒,宗教性质的募捐活动支持大学的发展,后来才逐渐多元化。[③]历史上宗教提供的公共生活、公共精神是一个分散和分离的社会重要的粘合剂。宗教不单是精神的守护神,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文明的守卫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与有组织的慈善其实是并行的。在中世纪,慈善包括任何可以取悦上帝的事:帮助穷人,装饰教堂,教育青年人,甚至包括保护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的攻击。教会也是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不是直接捐助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发放。中世纪的英国,每一座寺院都有责任收容乞丐,救助老弱病残,并安排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自救,同时也有权劝说或强迫其所辖范围内的有产者捐款济贫。[④]
二、宗教与慈善的分化
随着社会发展,慈善和宗教都有了不同的内涵和领域。随着宗教改革,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之于凯撒。世俗化成为基本的潮流,宗教回归于精神层面。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逐渐承担起更多的公共责任,历史上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责任被国家所承接,一部分由慈善组织承担的任务也被国家所承接。这点上东西方大体上是相同的。1601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济贫法》,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法规》,政府介入慈善事业,慈善活动在扶危济困之外有了更多的社会目标。慈善具有调节税收、世俗救济、政府和社会监督等新的内涵,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过渡。在中国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传统慈善也向现代慈善转变。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例,民国初年上海的慈善团体的慈善活动有了很大变化,它以济贫和职业教育为中心,试图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至于慈善原有的其他业务,则分别移交给医疗、教育、警察,消防等部门,或者被废止了,善举成为市政的起点,并开始被纳入到社会事业中。[⑤]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提供了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方位的服务。慈善的领域逐渐被压缩,在这一点上慈善与宗教又同病相怜,宗教的空间不但被世俗化所压缩,也被政治和政府所压缩,现代的政治领导人不再满足于政治领导人,他们也希望成为公众的导师乃至成为教主。于是我们看到,“上帝死了”和“慈善终结”都曾经嚣喧尘上。在20世纪初期乃至50年代初,西方一直有所谓慈善终结论,慈善失败论之说。英国讨论公益问题的拿但(Nathon)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所持的观最具有代表性:“我们历史中最悲?的失败之一,就是这些慈善者们所做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