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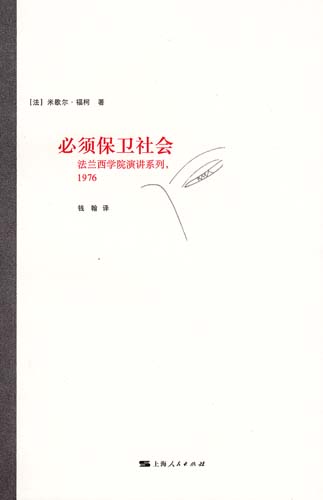 1964年3月13日凌晨4时,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的时候,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挟持,欲行强奸。基蒂·吉诺维斯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她的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在歹徒手中挣扎,却没有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杰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1964年3月13日凌晨4时,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的时候,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挟持,欲行强奸。基蒂·吉诺维斯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她的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在歹徒手中挣扎,却没有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杰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这一案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创造出“吉诺维斯综合征”这个名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的心理,经济学家用纳什均衡定理还计算里头的得失,社会学家则从公民道德建设的角度探讨事件的根源。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说过:“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诞生于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儿”。工业革命之后,急剧的社会变迁,驱使人们自觉地思考社会形式的构建,社会学因此得以在19世纪的西方诞生。也就是说,社会学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批判和重建的任务。对社会及其病症进行尖锐的批判,并提出解决方案,正是社会学,家的使命。这一使命,在1976年米歇尔·福柯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结集出版时得到了命名:必须保卫社会。
什么是好的、健全的社会?
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在他执教的大学里做过一个实验:让学生们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关禁闭三天,不许带收音机和闲书等消遣用品,也没有电视看,只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经典文学作品,他们会作何反应?90%的学生表示难以接受,会有剧烈的恐慌心理;只有极少数学生表示会愉快度过这段离群索居的生活。弗洛姆的结论是,如果去掉了自我逃避的麻醉剂——包括电影、电视、广播、体育比赛及报纸,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症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弗洛姆关于社会病症的观点来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因为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日益同仁的需要相对立,整个社会是可能得病的,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他提出了“社会神经症”的概念。他写道:“如果文明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如果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这两者的发展情形,我们就可以说许多文明制度——或者文明的各个时代和整个人类——都在文明进化潮流的重压下患了‘神经症’。”弗洛伊德说,人有病,还可以治疗;社会有病,却没有人能够迫使社会接受治疗。对社会神经症的敏锐分析看似没有什么用,但总会有人敢于进行研究——他们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
有病,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就是“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对“异化”的批判是很多学者、作家的共同选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说,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像《单向度的人》的小说版,生活越来越美好,强加在人身上的存在也越来越一致,但一些事物被视为无用而被无情摈弃,比如诗意、忧郁和苦闷;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19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20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将以暴力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锁定为社会重建的唯一道路,另一条路径则是早期大部分西方社会学家的主张,或通过道德重建、或合理化的改良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像弗洛姆,他设想中的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别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作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作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的人性力量。在这种社会中,人是中心,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此外,健全的社会让人在可以驾驭和认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使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动负责的参与者,使人成为他的生活的主人。”马尔库塞则将超越单向度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对象,一是哲学,使一部分人觉醒;一是所谓“亚阶层”,亦即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主体。——某种程度上,其实很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