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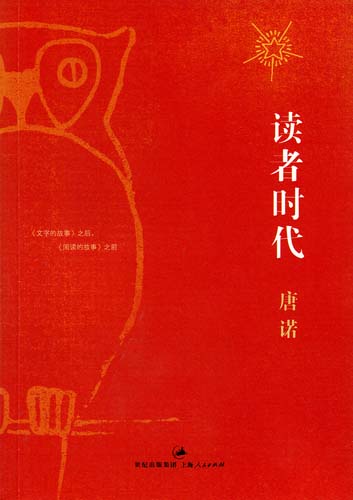 唐诺将自己与张大春,以及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均视为跨“制造书的人”与阅读者之界限,却“更珍视更享受”读者身份的一类,尽管非个体所能左右,但仍是“期盼一种纯粹读者时代的来临”。而《读者时代》就是唐诺对此心愿的一份努力了,在阅读的丛林里悠游,不是以六经注我,以我之色浸染外物,而是寻求阅读的多元可能性,“你隐约察觉这里头不晓得可装载多少新东西的看不到边界世界”,伸手触摸,那一种况味足以让你感知失落的灵魂。 唐诺将自己与张大春,以及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均视为跨“制造书的人”与阅读者之界限,却“更珍视更享受”读者身份的一类,尽管非个体所能左右,但仍是“期盼一种纯粹读者时代的来临”。而《读者时代》就是唐诺对此心愿的一份努力了,在阅读的丛林里悠游,不是以六经注我,以我之色浸染外物,而是寻求阅读的多元可能性,“你隐约察觉这里头不晓得可装载多少新东西的看不到边界世界”,伸手触摸,那一种况味足以让你感知失落的灵魂。
《读者时代》阐释一本本的书籍(亦含电影),也论述书背后的人,知人论世,此之谓也。唐诺的悠游,不是浮光掠影般的一瞥,而是基于极笨重的功夫之上。如讲述契诃夫——一双最干净的小说眼睛,非短时间可完成,而是从高中阶段的新潮文库开始,直到在北京三联书店买回十六册全集,历时近三十年,然后才得以透彻窥视契诃夫那“仿佛介于成品和素材之间,介于小说和民间生活史之间”的奇妙作品;对于梅特林克的《青鸟》,不仅有着从漫画书到文字书的逐渐演变,还有与幼年自家惨淡境况的暗自相合,青鸟又何尝仅仅是青鸟那么单纯?和侯孝贤的交情早在其未功成名就时,对其电影作品自然不必有神化色彩,而是追寻那永恒失落的最好时光,个体与时代在单行道上一去不返。
唐诺一本本书读去,自我设定的位置是进入,充满个人真切感受的进入。他讲格雷厄姆·格林,其小说“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布景搭建,而是用的真山真水,这样的道德景观,既是心志的,也是实体的,是文学剧场空间,也是历史真实空间”,其不合时宜处,如同我们内地先锋派文学盛行时,用写实手法写就的小说大受压抑,不见爱于新潮评论家之眼,不知格林始终未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无类似因素。唐诺看重格林的说故事能力,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文学国度的创建者,可称之为“格林之国”。但于此国度中,却是一个苍老之人注视着年轻的土地,看着一切凶险即将发生,却无人肯听他的预言,对于他而言,只有永恒的异乡。我们可以看到,唐诺的这种阅读进入,确是虔敬而真诚的,其寻求的是探究作家创作的底里,以平视的视角,拂动琴弦,既为自娱,亦召唤同调者。
未定于一尊、蕴涵多种可能性是阅读的乐趣与真谛所在,即谁也不知道在下一个街角会遇到什么。唐诺谈阿城的《常识与通识》,有他自己的发挥,“常识没什么了不得的,甚至说对说错都没那么要紧,而是它是鸡啼,是Morning Call,是清醒的声音,负责把我们唤回它所从来的、扎根的真实无欺世界,一个具象清明、朗朗乾坤的世界。”他或许与阿城达成了共识,也或许是自己从阅读中引申出这些,不论如何,唐诺在乎的是阅读的多层次性,既有阅读者的耐心细致,也要与书籍形成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关系,于契诃夫小说尤甚,因为非戏剧性、非概念化人物是其作品的特点,在如许丰富的可能性面前,阅读者无法按捺住解读与阐释的冲动。唐诺起始有拿契诃夫这些“美丽但无用”的小说不知如何是好的烦恼,但在身边的小说家朱天心、张大春对契诃夫的激赏之下,重读其全部作品,“努力地读和想,好像也有点懂了”。契诃夫的谦逊与温和,使其不会拿笔下的人物作为棋子,不会因顺应某种理念而修改事实,因此他的小说“凝聚不成某种雕像般刚硬的、截然的、和寻常世界划清界限的封闭性作品来”。而在谦逊之外,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成就了契诃夫如此干净的一双小说眼睛,其独特无人可以取代,因为源于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