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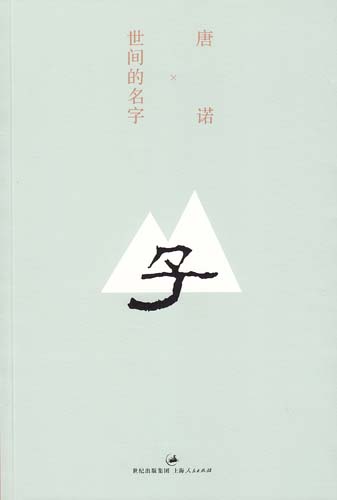 散文集《世间的名字》由20篇长文组成。从富翁到医生,从聋子到骗子,从编辑到主播,直到最为熟悉的小说家,均被唐诺信手拈来,并置一炉,打碎重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名字”。但他毕竟不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人类学家,也不是康德式的哲学家。他无意以形而上阐述世间诸般人物,不愿以清高的姿态俯视世人,更不欲对无处不在的陈规陋习、社会体制的诸多弊端做出道德上的评判。他饱读诗书,但始终只以普通读书人自居,满足于自我的小趣味,也受累于世事的纷扰。他对世间众生并无既定的成见,并不因为关系的亲疏而心生莫名的距离。他悠游于世间,读书识人看世界,一路行来、一径写来,偶尔从书斋探出头来打望这浮华世间,看到的不尽是他人的生活,或许更包括他自身的影子。 散文集《世间的名字》由20篇长文组成。从富翁到医生,从聋子到骗子,从编辑到主播,直到最为熟悉的小说家,均被唐诺信手拈来,并置一炉,打碎重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名字”。但他毕竟不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人类学家,也不是康德式的哲学家。他无意以形而上阐述世间诸般人物,不愿以清高的姿态俯视世人,更不欲对无处不在的陈规陋习、社会体制的诸多弊端做出道德上的评判。他饱读诗书,但始终只以普通读书人自居,满足于自我的小趣味,也受累于世事的纷扰。他对世间众生并无既定的成见,并不因为关系的亲疏而心生莫名的距离。他悠游于世间,读书识人看世界,一路行来、一径写来,偶尔从书斋探出头来打望这浮华世间,看到的不尽是他人的生活,或许更包括他自身的影子。
马尔克斯说,“人总有一件主要在做着的事。”或许,在唐诺看来,无论小说家、棋手,还是网球手,都坚守于各自的领域内,人生经历虽有云泥之别,却都有一件可以“做一生的事而且够认真”,都在与“生命的右墙”(极限)相互拉扯、较量,以期得到某种突破。比如,拉面师傅以面条书写自己的哲学,费德勒行云流水的扣杀仿佛极致的艺术,尽职的编辑念念不忘于“两千册的奇迹”这一难以逾越的出版黄金定律,男高音一次次用高亢的嗓音挑战生物学的极限……不惟如此,唐诺也在寻求写作的“右墙”,从《文字的故事》到《世间的名字》,他屡屡越界,医学、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甚至于商业分析、美食评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在世间生存,不同的人生、迥异的职业自然有各异的性情,其间也有不足与外人道出的隐衷,但他们并非孤立无援地存在,也有着这样那样微妙的交集。唐诺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共性,记录在案,也就有了笔下种种奇妙的类比。他说,图书市场如同体育竞技,如果“没困境没折磨”,球员不会苦练球技,同理推之,编辑也会逐渐丧失对好书的甄别能力。煮拉面好比写小说,都得仰仗于创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日复一日的操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骗子与四处巡演的过气歌手,更有着似曾相识的仿佛,他们游走四方,以浮夸的言辞、华丽的表演骗取他人的信任,获得物质或精神的满足。
说罢世态百相,《世间的名字》里更能见出唐诺的可爱与真性情。他时而调侃,时而嘲讽,从平常的事物中发掘出鲜见的趣味。《少尉》里,他从士官的徽章讲起,原本整齐划一、枯燥刻板的设计,却令他联想起原野里“满满盛开的花”、绿油油的树林以及夏夜里遥远、高渺的星空。《烟枪》一篇,他不遗余力地为烟民辩护(当然也包括屡遭排斥的自己),历数他们的种种不自由:被大众无端误解、被法律有意歧视,其委屈与无奈之情于字里行间漫溢而出。《小说家》中,他语带调侃,自嘲读书的一无是处,直言小说家的特权在于可以“虚构事物”,可以自由说谎而又“不附带刑责”的惩罚。然而,戏谑归戏谑,写作对于唐诺,仍是最为舒适、最为轻松的事情,是一片足够清朗恬适的自由之境。《书家》里,他寄希望于好友张大春能像“一株植物般拿着毛笔地老天荒的一直写下去”,这自然也是他的内心所愿。但面对书法的日渐式微,除了心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惋惜之外,大约也只有平静地接受现实了。
“这不是个芳香的世界,但的确是你居住的世界。” 唐诺引用雷蒙德·钱德勒的话为他的书写作结,无形中倒成了《世间的名字》的最佳注脚。这世界因为汇聚着“几百万心思、际遇、梦想、生命主张不一致的人”,“相互冲突彼此妨碍” ,故而有了种种不为人知的隐密心曲。《世间的名字》是一种“碎片”式的书写,每个碎片折射出世界的一片影子。所有的碎片汇集起来,构成了唐诺的整个世界。或许,这也应该是世界本来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