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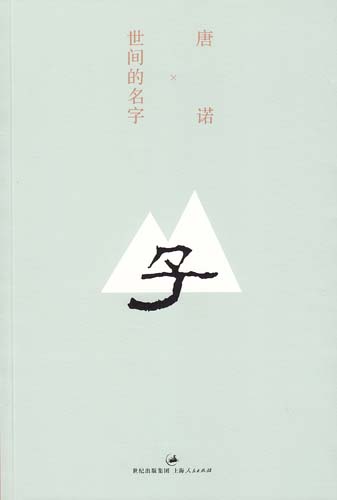 作为著名的文坛眷侣,唐诺和朱天心通常是一起出现,做活动、接受采访。不过,在此次文景艺文季的系列活动中,两人是一前一后来上海。这反而成了某种机缘,让唐诺暂时离开朱天心的“阴影”,充分发挥身为“专业读者”的特长,畅谈写作的追求、阅读的真相。 作为著名的文坛眷侣,唐诺和朱天心通常是一起出现,做活动、接受采访。不过,在此次文景艺文季的系列活动中,两人是一前一后来上海。这反而成了某种机缘,让唐诺暂时离开朱天心的“阴影”,充分发挥身为“专业读者”的特长,畅谈写作的追求、阅读的真相。
唐诺热爱阅读,人尽皆知。此次来上海,行色匆匆,他还利用采访间隙,背着包,站在下榻的酒店大堂里读了十几页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那只包,也有一些笑料——由于每逢出远门都带书,途中又难免逛书店添置新书,背带已不堪重负,断了两根。
这些还不算严重。在台北,唐诺通常早晨8点去咖啡馆,待到下午一两点,其间一直在写作。吸烟的他只能坐到室外,有各种噪音,还得忍受夏季38摄氏度以上、冬季10摄氏度以下的气温,“蛮痛苦的。”而不在家里写作的理由是:“每当写作遇到困难,我会去看书。但在咖啡馆就毫无机会,手上没书,写不出也要瞪着稿子两个小时跟它拼。对此,唐诺还总结了一句很哲学化的表述:“把自己逼到书写的前沿。”
曾经从事图书出版二十多年,尤其是作为“朱天心的丈夫”,唐诺本人长期隐身于幕后。他也安之若素,“我常常说,朱天文跟朱天心的小说是最重要的,我的书写不那么重要。”
两人高中即相识。那时唐诺编校刊,常约朱西宁的稿子,逐渐和他女儿天心熟络了。18岁那年朱天心写出长篇自传体小说《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又过几年,她嫁给了唐诺。
婚后,唐诺成为朱天心的“教练员”,大力促进其书写活动。《方舟上的日子》《向我眷村的兄弟们》《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等,都与唐诺息息相关。《学飞的盟盟》更如此,那是朱天心对女儿谢海盟成长历程的记述。
“对自己的职位,我还蛮骄傲的。”唐诺向记者笑言。
当然,在文坛,他亦有独立的地位。“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应该这样:把茶杯一摔,大叫‘我活得一点自我也没有’,可惜,完全不是这样。”作为“专业读者”,唐诺的《阅读时代》《阅读的故事》深受好评,他对推理小说的热衷,也颇有影响力。
前些年,唐诺离开图书业,专心写作。之所以到咖啡馆,除了“怕掉回阅读中”,还和心态有关。年轻时他和许多人一样,觉得外部世界充满了杂音,阅读和书写时最好把自己封闭起来。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产生了怀疑,“外界的声音应该是一种必要的提醒,是对书写的校正。这样,书写才不会像断线的风筝,仅仅是安慰自己,失去重力。”因此,他把书桌尽可能往前推,推到和外面世界交融的那一个点上。
由此,唐诺近年来的作品有了变化。《文字的故事》《世间的名字》,以及创作中的《尽头》,皆非只谈阅读,而呈现出令人惊艳的新气象。当然,阅读依然是无法舍弃的。有时候他和朱天心来上海跟谁也不打招呼,躲宾馆里看书,“结果被王安忆骂。”
两千册奇迹
“阅读,可以在浴缸里”
生活周刊:你提出过“两千册奇迹”,即在台湾,一本书平均能卖到两千册就可以保证书商存活了,新作《世间的名字》里有一篇《编辑》,提到近两年台湾书市不太好,这个定律有被打破之势。目前的情况如何?
唐诺:还好,相对来讲,台湾书市的稳定度比想象的要高,数据也显示了这种状况。当然这并不表示说,台湾书市像一张死亡心电图,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有些东西在变化。比方说书店的概念改变,以前一本书可以在书店存活三个月,现在可能只有两个礼拜。于是那些需要较长时间轮转的书就少了,畅销书更多了。但这不是阅读活动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商业条件变化了,使某些需要暂时没有被满足。
生活周刊:但大陆书市的确变化很大,实体书店、纸质阅读受到了来自网络的巨大冲击。
唐诺:我想只能说大陆的商业模式有变动,所以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但我看不出来人的阅读行为会有剧烈的变化,即便互联网会减损我们对需要消耗时间的阅读的耐心,可是也没有那么戏剧性。阅读本身是一种人类活动,也是成熟的行业,基本上,在哪里它都是稳定的。就是说,书的本质是多样、少量、利润微薄,永远不会是“大游戏”。阅读活动是长期的社会过程,需要长期的理解。
生活周刊:那作家本人呢?莫言有一次告诉我,作家的阅读有时候会变得非常职业化,缺乏趣味。对你来讲呢?
唐诺:我不认为。我曾经是个编辑,有些书能免费拿到,有些书看了人家还会给钱,其实不给钱我也会看,当然,这个不要告诉他们(笑)。我的意思是,阅读不会因此而不同。博尔赫斯讲过,作者只能写出他能够写的东西,而读者可以看任何想看的东西,所以,作家通常更喜欢自己是一个读者,因为阅读有无限的可能。
生活周刊:所以你说你对阅读环境的要求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