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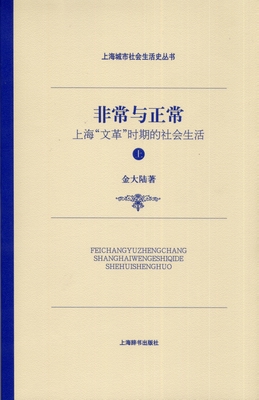 “文革”运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得进行,以至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在正常、非常的交错中,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灵魂的扭曲和变化。——金大陆 “文革”运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得进行,以至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在正常、非常的交错中,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灵魂的扭曲和变化。——金大陆
如何看待“文革”?这一问题困扰知识界二三十年,它甚至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站队的标尺。可“文革”十年,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是否只有政治挂帅,只有暴烈的政治运动,日常生活为政治所淹没?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的这本《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告诉读者,至少在上海,“文革”期间的上海日常生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在非常时期的“文革”期间,老百姓依然用他们的智慧和生存技巧努力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
《非常与正常》也可能是个特例,该书只立足于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它不涉及政治和运动的“文革”,直接进入家庭和社会生活,他写的是破“四旧”,抄家,“大串联”,收集和交换毛主席像章,红卫兵报刊和宣传品,上山下乡,“深挖洞”,“野营拉练”,学工学农学军,偷书与地下学习,“向阳院”,追查谣言,以及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时的社会反应等;更加不厌其烦的是罗列各种统计档案,比如人口状况(人口自然变动、机械变动、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婚姻管理(结婚仪式、结婚和离婚登记等)、计划生育、社会两性关系、职业与收入、物价与票证、服饰演变(崇武的审美到“奇装异服”)、蔬菜生产和供应(种类与价格等)、粮油供应(半两粮票的传说、国营粮店的贪污和浪费)、水产品和猪肉供应(关于肉票的集体记忆的失实)等,立体地展示了“文革”时期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金大陆通过对上海“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梳理,试图说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其总的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然而,即便处在运动高潮中,人们的生活还得进行,所以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括两个层次的“正常”态:“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金大陆表示,从社会生活看“文革”史,也就是从下往上看,看到的“文革”社会原像不那么脸谱化,不是只有凶神恶煞。“文革”当中的那个“群众”,还有一个求真、求美、求善的形象,这条线是存在的,也存在群众自发对于“文革”的反省。
“社会还在运行,人民还在生活”
东方早报:这本书名就叫“非常”与“正常”,这两个词除了是对“文革”时期上海日常生活描述和概括外,是否也是你的研究方法论?
金大陆:我在这套书的题记里说,“文革”运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得进行,以至在总的“非常”态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顺应之中的正常”和“应对之中的正常”。但在“顺应着”的正常中也有扭曲,在“应对着”的时候也有张狂。但在正常、非常的交错中,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灵魂的扭曲和变化。现在研究“文革”最大问题是脸谱化、简单化。如果我们从下往上看,我们看到的“文革”社会原像,就可能不是那么脸谱化了,不是只有凶神恶煞了。“文革”当中的那个“群众”,还有一个求真、求美、求善的形象,这条线是存在的,也存在群众自发对于“文革”的反省。
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做“文革”研究不是赞美“文革”,“文革”研究有很多论点,比如浩劫论等。有一路是继续追错,就是追集体错误;还有一路是认为“文革”是重大人类文化遗产。我认为都不对,我还是以史料为本,学术至上,还原本相。还有,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人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比如“文革”初期上海中学红卫兵女孩子穿的都是那种蓝裤子,可到了后期,同样一个学校女红卫兵,都穿花裙子白衬衫了。这就是一个社会变化。所以,“文革”在不同阶段的日常生活表述是不一样的。东方早报:一般谈到“文革”,都是在谈政治的“文革”,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之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怎么样,普通人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怎样,尤其是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