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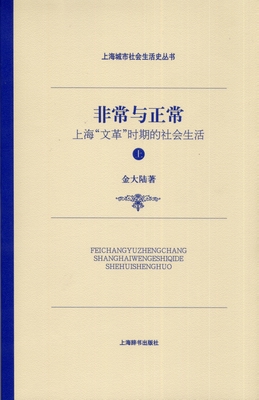 “抵制奇装异服” “抵制奇装异服”
据金大陆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所载,1975年7月19日下午,上海市服装鞋帽公司为建议有关组织“拟可开展一次抵制奇装异服的宣传教育活动”,遂在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和西藏路等上海主要繁华路段设岗,观察记录上海女性的着装情况。
事后据报告,约两小时内,上述地段共有1095位女子着裙子,其中裙长超过膝盖的为204位,占19%;齐膝盖的102位,占10%;膝盖以上一二寸的580位,占55%;膝盖以上三四寸乃至五六寸的超短裙亦有169位,占16%.
时隔一年,1976年7月,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亦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豫园、南京路、人民广场等闹市地区设点观察。事后汇报,在上海最负盛名的中百一店门口“仅15分钟内,就有40多个穿奇装异服、理怪发型的人走过”,而1976年的“奇装异服”有四大特点,其一为“长”,即衬衫包裹住臀部;其二为“尖”,如“燕尾领”等;其三,“露”,所谓身穿“薄型透明衬衫,内系深色胸罩”;其四则“艳”,如着一身“深咖啡、深蓝色”等。更有意思的是,据有关部门调查,当时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南京东路外滩,200米距离中就有600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其中将近200对“动作不正常”。
如果我们只是抱持惯常的历史认知,那予人一片肃杀消沉印象的“文革”时期,男男女女合该面色阴郁着装一律,这占总数16%的敢穿超短裙女性简直腐败透顶;青年恋爱虽属自然,但大街上光天化日“动作不正常”,则显然有悖主流道德观,纯为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上述两则材料,最富深意处,即一方面凸显出“文革”时期,极权政治和极左意识形态放肆侵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并无一例外地上纲上线至政治指控;但另一方面亦见出上海社会青年男女之求新求异求奇之风潜滋暗长,蓬勃发展到了要惊动有关部门设岗置哨的地步,互为攻守,既证明了“政治指对的虚妄和脆弱”,又印证了日常生活自有消融权力的妙招。
“非常”与“正常”的两种眼光
之所以拈出这两段故实,是因此正可看出《非常与正常》一书之特色。“文革”十年,不论其最终之意义厘析如何,就其事实层面而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搅动社会生活最剧烈的一场运动,在使社会局势和状态处于“非常”之中,然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不论如何总要进行下去,以至身处整体的“非常”状态下,个体时时需要“顺应之中的正常”以及“应对之中的正常”。前者按作者所言是“非常”的“调节机能的显示和表达”,多产生“正常中的扭曲”,后者则系“非常”的“制造功能的扩展和延伸”,多产生“正常中的妄为”。是故金先生所欲析解的“文革”话题,并非此前习见的高层权争抑或意识形态流变,这一建基于“政治运动的向度”所展开的讨论碍于资料的未完全公开和各种政治拘囿其实颇难充分研究,此即作者选择将“文革”研究向“社会生活的向度”垦拓的一大原因。
如此改弦更张,眼光照见处,反倒别有风光。全书以“上海1966年-1976年”为时空坐标,聚焦“社会生活史”,依凭多年积累的相关资料,举凡此时段内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各方面内容与发展情况尽皆阑入。如此构成的“文革”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多维全景画面,使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上海的‘文革’”,更是“‘文革’中的上海”;不仅是上海的“非常态”,更是“非常态”之下的上海如何艰难维持自己的“常态”,从而使“文革”研究“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换句话说,书中时时交叉两种眼光,一种是外部的、整体的,提供给我们观察上海“文革”社会生活时代背景的眼光,以明了种种造成“非常”的原因;另一种则是内部的、个体的,从群众日常立场出发的眼光,对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前者构成一种“对视”和“补充”。
革命也要吃菜
再者,此书亦未简单化对于文革“非常”状态中的权力评价,事实上,有时“非常”的政治骚扰也阴差阳错给民众带来实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