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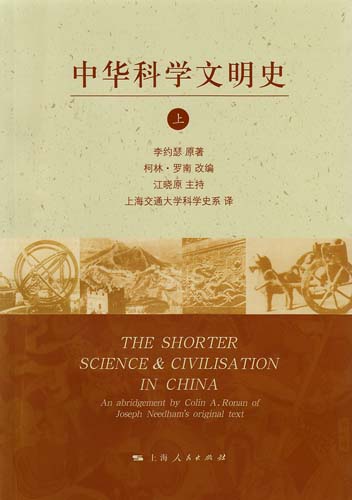 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缩编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读李约瑟,在感受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李约瑟难题”,并对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新的展望。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 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缩编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读李约瑟,在感受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李约瑟难题”,并对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新的展望。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
解放周末:在《中华科学文明史》封底上,刊登了您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李约瑟经典著作的经典浓缩,中国科技通史的权威版本”,对此您能否作进一步解读?
吴国盛:我的推荐语讲了两句话:它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是一部权威通史。这两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经典。李约瑟以其宏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开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之先河,堪称经典。而由柯林·罗南缩写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得到了李约瑟本人的认可,亦可称为经典缩写本。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特别适合普通读者阅读。
它是权威通史。某种意义上说,李书集成了、代表了中国科技史的整体成就,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式。李书虽然由李约瑟发起、策划、主笔,但实际上汇集了数十位东西方汉学家的智慧。与其巨大规模和篇幅可以相比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中国内地的科技史家集体编写、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后者除了材料更加扎实、丰富,编史纲领并无根本突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李书是一部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
解放周末:具体而言,李约瑟创造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范式和研究纲领?
吴国盛:有两个方面。首先,高度评价16世纪之前中国人的科学和文明成就。李约瑟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 (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知名的生物化学家)用英文写作的巨著,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点是中国人民在积贫积弱、备受国际社会冷落时特别感激的,也是中国科技史家自觉沿袭的编史目标。
其次,李书站在今日科学发展的视角来透视中国古代科技史,用今日的科学分科、今日的科学划界标准来编排古代中国的科技文明,是一部典型的辉格史。虽然李约瑟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知识方面远远走在西方的前列,但是,他仍然相信近代科学是一切文明发展的最终归宿。所有的原始科技,东方的、西方的,如一条条溪流汇入到近代科技文明这个“大海”中,都最终要发展到现代科学这样的形态,这是世界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科技史的“百川纳海”模型。因此,他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世界近代科技的先驱,强调它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和推动作用。这一编史模式也为中国科技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解放周末:能否举例说明?
吴国盛:比如,我们在李书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他就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技术成就的高低进行比较。李约瑟有非常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不仅熟悉中国的情况,也熟悉西方的情况,因此他能够做这样的技术性比较。我们经常可以在书中看到,他总是力图论证中国的某种技术、某种理论或观念比欧洲领先多少年,某种技术、思想或观念是近代科学的先导、先驱。
又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个如今的中国人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本土自古以来的说法,而是20世纪上半叶被李约瑟“炒热”的一个来自西方的说法。16世纪,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和西方历史的进程,但培根并没有说这些发明来自中国。19世纪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说法,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入造纸术,正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但是,让“四大发明”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正是李约瑟。
解放周末:李约瑟以西方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突出它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贡献,这种范式对此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吴国盛:在李书之后,中国内地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两部通史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上世纪80年代由杜石然等编著的单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部就是前面提到的上世纪90年代启动、2008年完成,由卢嘉锡总主编、中科院集结全国力量完成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者是一部小型的通史,做了一个初步的历史分期。后者则充实了大量资料,研究更为细致、具体。但是,总体而言,这两部书仍然是以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目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视野来编排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 (通史从而也就只能是分科史的简单拼接),在思路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李约瑟的范式,都还限定在李约瑟的“框框”之内。这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李书的权威、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