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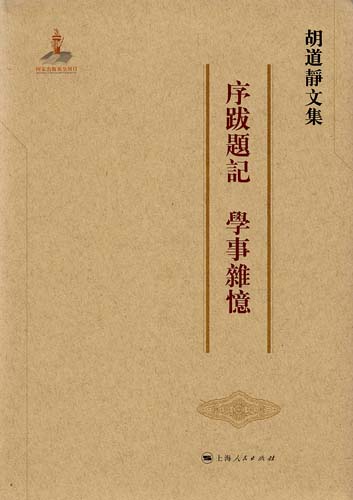 道静先生与李约瑟博士 道静先生与李约瑟博士
先说道静先生与李约瑟博士三十七年交谊、五次会晤的故事。
道静先生与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的交谊,可谓国际学术界的美谈。至于有关两位晤面的情事,则更具传奇色彩。作为道静先生的学生,我有幸见证了这两位国际科技史巨子的第三次会晤。
那是1981年的9月中旬,我从道静先生命我为他准备的一些会议材料中获悉,李约瑟博士与鲁桂珍博士应中国科学院之邀,在参加罗马尼亚召开的国际科技史学术讨论会后,于9月16日来华作第六次访问。除在北京有颇多学术交流外,在上海也有不少学术活动,其中包括与《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主编等会见。《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是由时任上海社联主席、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的罗竹老与道静先生一起策划、为李约瑟博士八十诞辰祝寿的巨著。罗竹老等得悉李约瑟博士访华的信息后,决定于李约瑟博士来上海开展学术活动之际,向他作一次当面汇报。道静先生要我准备的,正是那次会议的材料。
9月20日上午,抵沪后的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与罗竹老、朱东润先生(《中华文史论丛》主编)、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中国科技史探索》主编)、道静先生(《中国科技史探索》执行编辑),以及李俊民、钱伯城等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与《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的全体同仁等,在绍兴路5号的上海出版局二楼会议室亲切会见、晤谈,并在出版局大楼南侧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是日下午,道静先生兴冲冲回到办公室,高兴地告诉我:明天下午,李约瑟博士与鲁桂珍博士将赴其寓所作客; 经与主持社务工作的毛振珉副社长商定,要我以助手的身份,参加接待。这一安排,自然让我喜出望外。
对于李约瑟博士,我并不陌生,因为我已读过科学出版社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三、四、五卷(第二卷《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未出版),并略知了这位享誉全球的科学史家与“中国”相联系的一些传奇式的经历:1937年,赴剑桥留学的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三位中国留学生使这位剑桥冈维尔-凯思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深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刻苦的汉语学习;1942年至1947年,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学机构及任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期间,广泛考察和研究了中国历代文化遗迹与典籍;1948年返回剑桥后,在中国学者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协助下,开始撰写 《中国科学技术史》;1950年,发起成立英中友好协会,并亲任会长;1952年,参加“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委员会”,因此而一度遭受打击;1954年和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至197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四卷及第五卷若干分册先后面世。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读者,正是从李约瑟博士的这些著作中,惊讶地熟知这位对中国古代文明如此了如指掌的英国科学史家的。不过,对于我来说,自师从道静先生并得悉其与李约瑟博士的友谊后,似乎对这位“师伯”更有了一番别样的崇敬之情。
道静先生向我讲述了他与李约瑟博士订交与两次面晤的经过。那是1956年,李约瑟博士和道静先生分别读到了对方的科学史巨著——《梦溪笔谈校证》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彼此为对方的学识所折服。自1958年起,传书鸿雁在两位科学史学者之间架起了学术的桥梁。至“文革”前,往来信札已达百余通。1964年10月,李约瑟夫妇第三次访华(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博士于1952年第一次访华,1956年第二次访华),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参加国庆观礼后,来到上海,在锦江宾馆会晤了“农夫模样”(李约瑟语)的道静先生,并畅谈至深夜。1972年10月,李约瑟博士第四次访华,其时,虽值中国“文革”动乱,但他还是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指名要会见道静先生,“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竟诓骗说:胡道静已经死了。李约瑟博士自然无法相信。1978年夏,李约瑟博士在日本友人那里得到“胡道静仍健在”的确讯,由日赴华,作第五次访问时,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同志的过问,才在上海第二次见到道静先生。当时,李约瑟博士对市接待部门的要求是:“诣府访谒”。
道静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不无唏嘘地对我说:你也知道,那时,我人虽然放出来了,但家里,不光是小,还一塌糊涂,哪能接待外宾?市里也晓得这情况。所以一方面坦率地告诉老博士:道静先生住房困难的缓解正在落实之中,去府上访谒的愿望以后一定能实现;一方面通知我,仍去锦江宾馆与老博士面晤。就这样,经“文革”浩劫后重逢的这对国际学术友人的双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1980年夏,在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亲自安排下,道静先生的住房困难总算得以缓解,从逼仄的旧宅搬进了新建的四平大楼;1981年9月,是李约瑟博士第六次访华,“诣道静先生之府访谒”的愿望终于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