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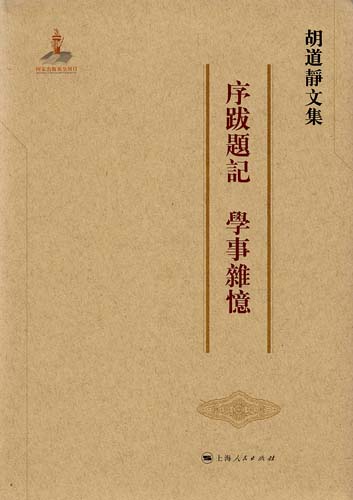 1976年道静先生从提蓝桥“赦”出后,被安排在虹口区清洁管理所“监督劳动”。道静先生说:我是一个捏惯“小笔头”(指笔)的人,到了那里能做啥?唉!他们居然叫我捏“大笔头”(指扫帚),去扫一条叫“甜爱路”的马路。那时候的老天爷也真会捉弄人——我是苦得勿能再苦、恨得勿能再恨,他们居然要我一个又苦又恨的人去扫一条又甜又爱的马路! 1976年道静先生从提蓝桥“赦”出后,被安排在虹口区清洁管理所“监督劳动”。道静先生说:我是一个捏惯“小笔头”(指笔)的人,到了那里能做啥?唉!他们居然叫我捏“大笔头”(指扫帚),去扫一条叫“甜爱路”的马路。那时候的老天爷也真会捉弄人——我是苦得勿能再苦、恨得勿能再恨,他们居然要我一个又苦又恨的人去扫一条又甜又爱的马路!
今年清明前夕的3月29日,我和道静先生的子女陪着九十五岁高龄的师母来到松江天马山公墓,祭拜在这里已长眠了十个年头的胡道静先生。山陵穆穆,苍天朗朗。凝视着道静先生慈祥的遗像和供奉在其灵前、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胡道静文集》,听道静先生笑谈人生酸甜苦辣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
这是一个关于“文曲星下凡”的故事。不过,要讲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道静先生全家的乔迁说起。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汪道涵市长亲自过问,道静先生全家从五十年代蜗居到八十年代的虹口浙兴里迁往四平大楼。
坐落在四平路大连路口的四平大楼,原是一幢非居民住宅楼。七十年代末峻工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为解落实政策的高级知识分子居住条件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急令将这幢大楼改建为住宅楼,即在每一单元隔出厨房与厕所,以与居住房间“配套”。自然,这样的住房,其逼仄程度可想而知。就拿汪市长为道静先生安排的那套住房为例,其北,是一个层面住房的长廊式通道。进得房门,左侧是“硬”隔出的厨房与厕所,右侧即是一十平方左右的小间;走过厨房厕所与小间相对的过道,便到了既是客厅又是房间的一个南向大间;这一大间左侧另有一南窗小间,亦约十个平方。实际上,只是一个两小室一大厅、外加各约两个平方厨卫的一套居室。尽管如此,当时真可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以,已到需经上海最高领导首肯才得以进入之不易程度。
由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宋原放同志安排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的道静先生,又由汪道涵市长的关怀而分配得四平大楼十楼的一个单元新住房,怎不欣喜与激动万分?在我替他去市房地局办好入住手续的当天,他便兴冲冲地领着我坐14路无轨电车到了浙兴里老房子。这是道静先生五十年代初从新疆回到上海后,一位至友让其安顿在这里的。道静先生的书房,是一个需要架梯而上的阁楼。殊料,一住就是十余年。“文革”期间,道静先生身陷囹圄,师母与几个孩子在此苦苦挣扎。现在,终于有了稍大一点的新房,自然好不喜欢。那天,道静先生兴致勃勃地让我随他爬上阁楼,参观了他的书房;兴高采烈地与大家围坐在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由师母做的午餐。自然,其后便是一系列置新理旧、乔迁安置的忙碌。
数月后,我得悉道静先生的新居布置已经定当,便登门贺喜。随着笑吟吟的师母踏进新房,只见进门右侧的小间已设有双人铺位,成了两个孩子的寝室;南向的大间,既是两老的寝室,也是会客之处;大间右侧那间带南窗的小间,则是道静先生的书房——“海隅书库”。进得道静先生的书房,他老人家满面春风,连连招呼就坐。
我在道静先生书桌一侧坐定,抬头便见书橱一侧的一幅《红梅图》。只见图中虬枝苍劲,红梅俏丽;布局有致,其趣昂然;图中题词,寓意风骨。于是,便向道静先生询问来历。于是,道静先生便讲出了那回“文曲星下凡”的故事——
1976年,道静先生从提蓝桥“赦”出后,被安排在虹口区清洁管理所“监督劳动”。道静先生说:我是一个捏惯“小笔头”(指笔)的人,到了那里能做啥?唉!他们居然叫我捏“大笔头”(指扫帚),去扫一条叫“甜爱路”的马路。那时候的老天爷也真会捉弄人——我是苦得勿能再苦、恨得勿能再恨,他们居然要我一个又苦又恨的人去扫一条又甜又爱的马路!当然,那时也没办法,我只得扫扫停停、停停扫扫,在甜爱路上苦恨度日。
一天,道静先生扫过一家人家门口,只听得一扇半掩的门里轻轻传出一声问话声音:“侬阿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有力。道静先生抬头望去,只见一位比自己略为年轻一点的男子在屋间和善地望着他。道静先生虽曾受牢狱之辱,但心智不屈,诙谐如常,机智地反问道:“侬——,是从啥地方看出来咯呢?”不料,那男子更为幽默,居然回答说:“我是从格林威治望远镜里看出来咯呀!”两颗相知的心,就这样在凌厉的寒风中热烈地温暖了对方。这位男子,就是后来成为道静先生莫逆之交的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仲威先生。
孙仲威先生,名桂恩,号仲威。生于1917年,山东蓬莱人。幼年随父旅居京师,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熏陶。曾拜花鸟画家于非闇为师,又受张大千指导。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法律系、成都齐鲁大学历史社会系。1949年进上海博物馆工作,为抢救大量珍贵国宝作出贡献。
道静先生冤案平反后,孙仲威先生特意作《红梅图》相贺,以颂道静先生“傲霜斗雪”不屈之志。正是这幅《红梅图》,让我从中知道了这个“文曲星的故事”。
|